姜涛,1970年生于天津,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后攻读中文系研究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好消息》《我们共同的美好生活》,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和诗》《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年代的中国小说》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王瑶学术奖青年著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东荡子诗歌批评奖”、“金沙诗歌奖理论批评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奖项。本文原题为《诗歌批评浓郁紧张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写作和解读的新向度——姜涛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姜涛
姜涛
崖丽娟:姜涛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中给我机会完成这次访谈。去年诗人、批评家张桃洲教授《我特别希望树立起“姜涛的诗歌批评”这座标杆》一文引起关注。您从事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歌研究已经30年, 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张教授说“(姜涛诗歌批评)这个标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尺度,以之去衡量当下诗歌创作和批评,厘定诗歌批评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诚如张教授所言,在文学批评领域,恐怕没有比诗歌批评更充满争议的了。您进行诗歌批评的志趣因何而来,秉持的批评标准、原则是什么。
姜涛:丽娟老师好!桃洲的文章是一次讨论会发言的整理,感谢他的鼓励,但老朋友的表扬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千万不可当真的。我最初写一点诗歌批评,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写作中的困惑,也顺带整理一下阅读当代诗歌的感受。后来这件事做得还算顺手,就歪打正着,不断写了下去。但诗歌批评,在我这里仍然是某种“副业”,自己的主业是在学院里教书、做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可能正因为是“副业”,心态倒也放松,不必特别关注“现场”的种种,跟进什么最新的动态,更可推卸“表扬”的任务,只是在自己关心的问题脉络上,根据此时此刻的心境发言。
正像你提到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内,诗歌批评的位置有点特殊,这大概和当代诗的基本文化处境有关。怎么说呢,新诗这一文体的发生,虽然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下沉、解体的结果,一开始包含了平民化的面向,但由于先锋性、精英性的取向,也不得不一直扮演了某种文化异端的角色,处在重重争议之中。这种状况在朦胧诗之后的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始终摸爬滚打,在共同的磨砺中成长,批评主要起到一种辩护、说明、保驾护航的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为诗一辩”的态度,也可能会导致某种内倾性、封闭性。比如,针对外界误解和非议的抗辩,对于诗人诗作的细致分析,如果缺乏内在的紧张感,难免也会陷入某种感知和观念的“舒适区”,变成对现代诗学一些基本原则的反复重申。更低级一点的表现,就是“诗歌批评”蜕变为“诗歌表扬”,无论什么诗集出版、什么样的诗人出现,出于私人情谊或诗坛关系,按需生产一些细读或评价的文字。这样的话,“诗歌批评”好像成了一种服务行业,只是寄生于看似热闹其实内卷的文学生意之中。
诗歌批评应该有更远大一点的抱负,在阐发诗歌形式奥义和独特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能澄清一个时期观念上的迷思,通过审慎的、有想象力的写作,来提供一种好的判断力,塑造更活跃、也更严肃的诗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也包括适度的紧张感,这就是说,能时刻对可能落入“舒适区”的感知结构、观念结构,保持一种反思的敏感。更强力的批评,是将当代诗的讨论放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中去展开,在诗歌写作、阅读与其他文学、艺术、人文知识工作之间,创造积极的内在联动,回应总体性的思想课题。正如常被人称道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释那样,使诗歌仍能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经验中耀眼且深邃的部分。
崖丽娟:您刚才说,诗歌写作和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的确如此。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兼事批评成为风尚,有一个原因似可归结于批评对解读当代诗歌的无力。批评家、诗人冷霜在《分叉的想象》一书中对“诗人批评家”现象研究颇为深入。前不久,青年诗人赵目珍也把这一现象的研究课题结集出版《探索未知的诗学》。诗人的批评术语与批评家的批评术语确实存在微妙不同,为理解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视角。作为学者、诗人、批评家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姜涛:对诗人批评家的关注,确实不是一个新话题,冷霜的文章应该就是他20多年前的硕士论文。我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一般批评的无效、无力是其中之一,但不一定就是主要原因。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诗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意识、反思意识极强的写作,诗人批评家更是不胜枚举。先不说外国的“洋大师”们,仅就20世纪的新诗而言,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梁宗岱、废名、艾青、袁可嘉,哪个不是重要的批评者。
诗人的术语和批评家的术语,确实会有微妙的不同,特别是诗人批评不必有论文腔、学院腔,往往更挥洒,更能凸显个人的才情。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差异,我也认为不是什么本质性的,因为诗人的批评和批评家的批评,生成于共同的知识氛围和当代文艺的圈子中,引述的资源、依托的观念以及可能的毛病,或许都差不多。就像学院化的批评,常被认为是概念化的、笼统和没有才情的。在追求个人风格的诗人批评那里,这样的问题可能同样存在。一些所谓的诗人批评看似洒脱,实际也不免笼统、偏执,甚至更喜欢搬弄概念。不是说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就一定会避免思维的直观和僵硬。
崖丽娟:从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主编的《雅努斯的面孔》诗歌丛刊专辑里的三篇文章题目《一份提纲:诗还有未来吗?》《诗歌何用?》《现代诗教漫议:何谓正常的写作?》可窥见现代诗学面临诸多自身难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当下新诗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前景如何,其发展有规律可循吗?什么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诗人何为?抱歉,每一个问题都太宏大,请择其一二回答吧。
姜涛:这些问题确实很宏大,也不太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但写诗的朋友们能不断提问,不断构想诗歌的可能性和文化位置,还是好的,说明当代诗的自我意识还是相当活跃,没有停留在前面说的“舒适区”里,只是依据一些现代诗的原则或“惯性”将当下状况看作是自明、自足的。我个人感觉,近年来确实有不少诗友在思考当代诗的新前景,比如,为了突破“现代性”逻辑提出“当代性”的问题;通过借镜传统或重申浪漫主义,希望能纠正现代诗的否定性、碎片化美学,赋予诗歌写作一种浑然的整体感和超越性;或站在尼采式的“反历史主义”立场上,强调诗歌与时代的对峙,凸显“不合时宜”的精神肖像;或者,希望强化与其他的人文思想工作的内在联动,破除那种直观化的“个人”感知,为当代诗的写作和阅读注入更多的思想力和现实感。这些思考选取的路径不同,所依托的对于当下现实情境的判断也迥异,彼此之间甚至是冲突、对立的,但这样的局面要好过大家闷头自顾自写所谓“好诗”的状态。事实上,现代及当代诗歌观念和美学的活力,都是涌现于观念和价值立场激烈冲突或发生转换的时刻,一种浓郁、紧张的氛围,往往有助于激发新的写作和解读向度。刚才提到的几种讨论,还是发生在局部,尚不能形成什么大的潮流,但局部也是好的,至少有一点制造氛围的效果。
崖丽娟: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同时颁给了学院派、民间写作的两位代表性诗人,由此而联想到九十年代那场影响很大的“盘峰论争”,现在回过头来看,与当下众声喧哗却语焉不详的网络批评声音(包括一些“网暴”现象)相比,这场论战在当代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大还是消极影响大?
姜涛: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好像有所关联。当年造成“盘峰论争”的原因很复杂,甚至涉及诗坛话语权和出版资源的争夺,有一部分是意气之争,不完全是诗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当代先锋诗歌内部的“共同体意识”由此瓦解了,这可能是消极的影响吧。但现在回头来看,相比于后来网络上的一些喧哗、乃至一些网暴,“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论战还是很有质量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并非只是泡沫的话题,像如何理解诗人的文化位置和角色,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的场景中,批判性的视角如何持续有效?如何理解写作和外来影响、理论话语的关系?如何理解诗歌语言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包括如何看待当代诗歌取得进展的同时自我封闭、固化的可能?这些讨论都包含了真实的诗学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而且,在更大一点的视野中,在90年代其他人文思想和知识领域,类似的论战或分裂也在发生,这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矛盾的显露有关。和80年代“改开”意识状态下,国家、社会和知识界有大致的共识不同,9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文化的走向,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诗歌界的争论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的争论有某种同构性,都在一定程度塑造了后来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的分化。还有一点,和其他人文知识领域发生的争论相仿,由于论争的双方你来我往,执着于各自的立场,有比较强的阵营意识、攻防意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特别深入的展开。记得当时臧棣的一篇短文章,给周边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贴标签的话,臧棣应该算“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代表,但他却认为“民间”一方对诗歌写作过度知识化的批评是有合理性的,诗歌和知识的关系并不是自明的,需要做更多的检讨,他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的命题。这样的思考突破了论争设定的逻辑,将问题翻转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是论争中为数不多非常有启发性的发言。实际上,这个话题还可进一步延展:在一个专业化、知识和感受不断分化的现实情境中,如果“诗歌是一种特殊知识”,那么这种特殊性怎么理解?如果仅仅将“特殊性”理解为想象力、感受力,那是否一定程度还是默认了现有的知识分化格局?其实,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诗歌往往和人类更高级、更有整体性的认知能力相关,诗歌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殊性”,是否可以包含对现代知识分化格局的突破意识、不同认知领域的联动意识以及情感和认知更深层的综合意识?对于开放当代诗歌的问题视野,这样的讨论都有必要持续而且深化。
崖丽娟:从学术角度分析,诗人代际以十年来划分是否科学有效?如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这样是否更有利于彼此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辨识,抑或相反。女诗人安琪倡导过“中间代”;张桃洲教授对“70后”学人、诗人也有过精辟论述。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姜涛:代际的话题,时不时会被谈起,好像每隔十年,自动会有一代人登上舞台。这样大致说说,倒也无妨,可较真一点的话,“代际”的出现,并不是简单依据自然年龄的差距。“同一代人”的感觉和意识,更多还是由特定的历史经验来塑造,在社会状况和文化潮流剧烈变动的时期,往往会将一代人推向前台。而且,即便是同代人,由于社会位置的差异和不同的价值立场,也不一定就有共同的代际感受。过去了的 20世纪,因为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世纪、社会持续重造的世纪,变动的节奏很快,大概每过十年就会一大变,这样也形成了一种印象,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代人。但这种代际节奏,是不是可以持续,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在文学的意义上,能否构成一个新的世代,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创造出新的文学可能,带来风气和观念的转变。
当代批评有一个可以检讨的积习,那就是喜欢频繁发明各种标签,身份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这些区分性、归类性的说法,不是不可成立,也会带来新的视角,但希望更耐心一些、更审慎一些,不必匆匆忙忙,只是作为一种标签随意张贴,或一个大个箩筐,将不同的人和事囫囵装入其中。这么操作会具有话题性,吸引一些眼球,实际价值却可能没有提倡者期待的那样大。
崖丽娟:以下问题同样困惑关心诗歌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语境的变迁,尤其是自媒体的勃兴,极大改变了诗歌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现在诗歌写作非常活跃,日产量之高可以用盛世来形容;与此同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频遭质疑。积极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文本大量诞生;悲观看法判断标准主要是读者数量锐减。评价新诗有哪些基本标准?
姜涛:新媒介的发展,极大改变了诗歌的生态,带来传播、交流便利的同时,难免也会泥沙俱下,抱平常心来看待即可。本来,文学的标准在历史中始终在变动,像朱自清当年辨析的,文学阅读的传统标准是百读不厌,但在一个民主化、平民化的时代,雅俗共赏也可以是新的标准。再比如,古典诗歌推崇温柔敦厚的美学,但在革命、战争的年代,爱憎分明也会成为新的美学、新的标准。
至于新诗的标准问题,一直以来就纷纷扰扰,好像很难取得共识。希望能确立稳定的标准、规范,好让新诗编入唐诗宋词的中国诗歌家谱的,大有人在。深谙新诗“现代性”品质的诗人和批评家,却会强调挣脱传统给定的感受方式,不断自我刷新,才是新诗最值得珍惜的活力。这样的分歧不会轻易化解,保持一定的分歧和对话,也没什么不好。形成标准的共识很难,但这不是说,在具体的个人阅读和判断中不存在标准。一些基本的文学标准,也包括传统的文学评价尺度,还是起到支撑性的作用。诗人席亚兵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古人所谓“二十四诗品”,可以重新引入到现代诗的评价,比如,先有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不同的风格和功能设定,再来讨论相应的标准,这样避免了判断的单一,更有助于现代诗多元美学的成熟。这是一个可以玩味的思路。再有,从批评和研究的角度看,标准不完全只是形式和美学的,也会包含一些更整体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考虑,比如,一种写作是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位置和功能,或者在向更多人敞开的过程中,提供了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
崖丽娟:我发现您在做诗歌研究的同时,还做诗歌普及或诗歌教育工作。2010年您曾参与由钱理群、洪子诚主编的《诗歌读本》编辑工作,您编著的是“大学卷”。您怎样看待大学教育对诗人的意义?1994年您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弃理从文,直接考了该校中文系读研究生,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毕业后留系任教至今。您的经历是否可以佐证您的观点?
姜涛:诗歌“普及”的工作,我做的并不很多。钱老师、洪老师主编的那套《诗歌读本》分为“学前”、“小学”、“中学”、“大学”、“老年及儿童”几卷,贯穿的是钱老师提出的“诗歌伴你一生”的构想。这套读本面向一般的读者,目的不完全在诗歌的“普及”,更偏重于“诗教”的一面,强调诗歌对于审美感受力的开启、情感的教育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作用。“诗教”是一个传统概念,现代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以个体内面的自由为前提,看起来与强调社会功能的“诗教”距离较远,可事实上,现代诗的阅读和接受,也提供了一种人格养成的方式,或者说,也包含了一种“现代诗教”的可能。前面的提问中,好像也提到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
我当时编选“大学卷”的时候,对于钱老师的想法领会不深,更多还是从现代诗自身的立场出发,视野虽然扩张到了诗歌阅读、诗人形象、诗歌翻译等方面,但主要还是面向现代诗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更偏重“为现代诗一辩”的态度。如果有机会重编这个读本,我可能会多考虑一些“诗教”的因素,更多考虑诗歌和现代中国人精神形式、情感结构的联系。再补充一点,按一般理解,诗歌的“普及”和“教育”就是让更多读者接受诗歌、了解诗歌,这对于诗歌文化的培植而言,这自然很重要。然而,“普及”不完全是单向的,按照老套的说法,“普及”也伴随了“提高”,当你不只是在小小的诗人共同体内部思考问题,而考虑通过诗歌与更多的人建立关联,那么你的思考方向和感知方向,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从“诗教”入手的思考,也会为诗歌写作打开新的面向。
说到大学教育和诗人的关系,我想这里的“大学教育”不是指一般的学院专业教育吧?物理系、数学系、计算机系的教育,哪怕是中文系的教育,与是不是写诗,关系应该都不大。大学能提供的主要还是一种阅读、交流和感知氛围,在当代诗歌的展开中,很多高校也是重要的策源地,这个不用多说。说到我自己,最初写诗确实和八九十年代之交北京高校浓郁的文学氛围相关,如果不是参加了校内的文学社团,人生的轨迹会有很大不同。我自己“弃工从文”,最后留在学院里以文学为业,只是个人的选择,其中有一些偶然性,并没有特别值得解释、引申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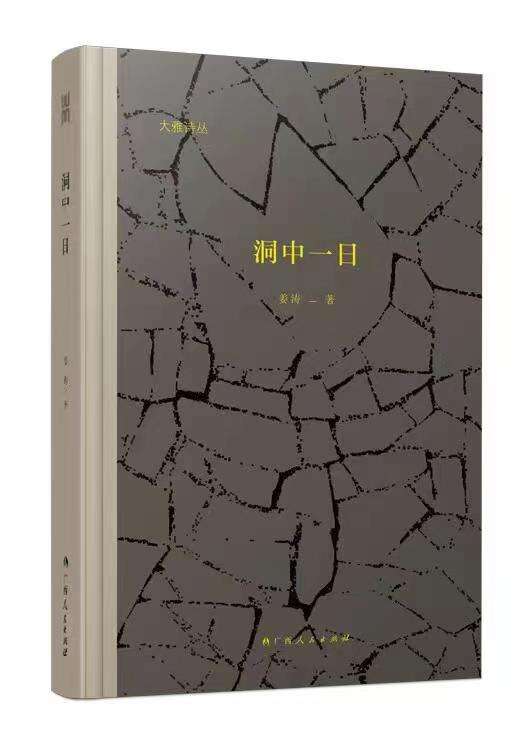 姜涛《洞中一日》
姜涛《洞中一日》
崖丽娟:前面我们用了较大篇幅讨论您的诗歌批评,现在请谈谈您的诗歌创作。迄今,您先后出版4部诗集。2020年诗人、评论家、学者周伟驰对您的诗歌创作进行过深入批评。除了诗歌批评,您的诗艺同样为同行称道。新诗集《洞中一日》与早期诗集《鸟经》比较,感觉创作风格变化挺大的,这种变化是人生积淀还是艺术追求?
姜涛:伟驰兄的文章写得非常细致,也很有洞察力。我觉得他的意图,是通过检讨某个人的写作,来回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诗歌青年”的蜕变史,顺便带出不同时期的文学氛围和群体心态的勾勒。这是我读的时候感觉最会心的部分。我写诗的时间应该不算短了,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个人的轨迹和当代诗歌风气的转换也有一定的呼应。大学时代,最初习作的抒情意味较浓,喜欢用一些自然或宗教性的意象,还有祈祷的语气,这和当年海子的覆盖性影响,以及对里尔克的阅读有关。后来,转而追求修辞的密度和包容性,写了一批技巧繁复过于冗赘的组诗,这与90年代诗歌“综合性”观念的激励大有关联。大致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更多写作的自觉,主动降低语言密度,尽量写得更放松、更精准一些,也将题材范围,缩减至个人情感和周边的社会和社区生活,试图在“微讽”距离中形成某种洞察。这其中有特殊的个人趣味,可总体上说,还是在90年代之后“个人化”写作的惯习之中。这些年写得少了,甚至基本停笔,除了忙于其他工作,无力分身之外,更内在的原因是,那种旁观、冷峭、有点虚无的态度,已成了某种感受力的痂壳,不能激发新的写作欲望和活力。当然今后还会有写作的规划,希望那时能一定程度走出“个人化”的峡谷,在相对高一点、宽阔一点的地方,首先更新一下自我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
崖丽娟:北大是新诗的母校。其实,清华大学也有非常光荣的诗歌传统。北大诗脉与清华诗脉二者似乎互为渗透又各呈异彩。您的好朋友、诗人、批评家、清华大学教授西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百年清华诗脉》。你们的经历挺有意思的,他曾求学于北大,现任职于清华,您曾求学于清华,现在任职于北大。西渡的博士生、青年诗人王家铭主编“清华学生诗选”《那无限飞奔的人》刚出版,您和西渡都写了推荐语。理科生与文科生写诗的差异性大吗?
姜涛:北大和清华,互为隔壁,常被拿出来比较。北大是新诗发生的摇篮,北大百年诗脉也没有断绝。清华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50年代院系调整后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清华的文脉、诗脉即便没完全中断,还是受了不小的影响。我在清华读到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文学社,在比较枯燥的理工科环境中,还有一小撮终日无所事事,喜欢闲聊和写诗的人,感觉惊喜又意外。后来又进一步发现,这一小撮写诗人,基本都是校园里的“异端”分子,不怎么认同当时学校里的主流价值,也不愿意参与“考托”、“下海”等潮流,与其说是因共同的文学旨趣,不如说出于对周围环境不满、活跃的天性以及对更生动思想交流的需求,才凑在一起、抱团取暖的。这种状况和隔壁的北大诗友或许十分不同,特别是,这个小团体没有太多参与当代诗坛的意识和抱负,心境更为素朴、浪漫,文学活动更多以喝酒、唱歌、“秉烛夜游”等共同生活的形式展开。简单说,大家不太把写诗当成一个专业、一个可作未来“志业”的行当,更看重的,似乎是以诗为媒介形成的兄弟情谊以及某种热烈又严正的态度。这是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状况。后来清华的文科发展很快,校园内的人文气氛更为浓郁,文学活动的展开方式,应该有很大的变化,应该更丰富多样了。这是我不太了解的,家铭最新编选的清华诗集,收录的就是更为晚近的新世代校园作者的作品。记得两三年前,有一次参加西渡、格非二位老师组织的“青年诗人工作坊”,在清华文创中心轻奢又古雅的小楼里,一众诗友高谈阔论,当时就颇感慨:清华园中有如此高尚的、可以谈诗的空间,在20年前不可想象的。那时清华写诗的朋友,好像只配坐在路边、操场或草地上,各自抱了一瓶啤酒,在黑暗里说话。
崖丽娟: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新诗是从外国现代诗引进和演变的,不读外国诗写不好中国新诗。另一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意境、意象、象征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翻译腔”无助亦无益于中国新诗发展。作为学者、研究者、译者,您在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面有哪些具体感受和建议?
姜涛:如何看待外来影响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新诗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翻来覆去,像一个解不开的连环套。这样的争议既是一种客观实存,又是一种认识的“装置”,有时需要绕开孰是孰非的判断,追问一下争议生成的特殊语境和文化逻辑。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郑敏先生批评新诗断裂于传统,观点并不新鲜,影响为什么很大,这和90年代初反思激进主义的文化守成思潮,就有很大关系。追问争议的生成语境,会在一定程度将中外、古今的关系理解为动态的、诠释性的,避免抽象、孤立地看待问题。无论“化欧”还是“化古”,都是新诗十分内在的要求,如果刻意构造对立,那或许是一种认识上的“强迫症”,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还有两点提醒:其一,外国诗歌的影响和传统资源的转化,对新诗的展开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否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从某个角度说,要把握新诗自身的主体性,还是要着眼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新诗人对于新的语言形式、新的想象力的构想和实验,离不开对外部和传统的参照、借鉴,但更根本的,还是基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基于对现代中国人自身历史经验的开掘和表现。其二,无论“外来影响”,还是“传统资源”,都不能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看待,其中的差异很大,构成非常复杂,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只是在自身的脉络中转化、承袭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到“传统”,一般的批评和解读的关注点,总落在文学层面,如象征、意境、意象等等。事实上,对于诗歌写作发生影响的“传统”并不局限于“古典诗歌”这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古典传统的存在,文学和审美之外,也涉及政治理想、社会伦理和人格修养多个方面。张枣在早年的一篇短文中曾说:“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是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这个说法隐含的态度,便不只是文学意义上,更指向一种文化和生活的整体,“传统”提供的是一种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顿自我、敞开自我,以及如何形成完满人格的路径。当然,这些看法都是很多朋友的共识,这里也只是大致说说。
崖丽娟:感谢您坦诚问答。
姜涛:感谢您精彩问题。
2023年1月24日春节。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