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策划推出“大国科学家”系列稿件,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集中展示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与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老科学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采集挖掘。
□ 公道北
1939年8月,重庆山城正处于高温之中,天空中的日军轰炸机正源源不断扔下炸弹,烧毁了半个市区。陪都郊区的南开中学也未能幸免,一片硝烟弥漫。
正是在这场轰炸中,16岁的郭可信身上留下了一块5分硬币大小的永久伤疤。很多年后,他对当年的场景依然刻骨铭心,“听到炸弹与空气摩擦发生的沙沙声,觉得离我们还远。谁知突然刺耳尖声大作,我们赶快卧倒在地,接着就是接连不断的炸弹的爆破声,天崩地裂,泥土树枝铺天盖地飞来,背上一处疼痛难忍。我还以为被弹片击中,后来才知是被一块落下的红热泥巴灼伤,衬衣烧了一个洞,我背上多了一个疤。起来一看,好险!不到30米,附近的树都被拦腰斩断。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机中、敌机的轰炸中成长起来的,国家概念比较强,民族意识比较深。毕业六十年了,无论是在海外求学,还是在国内工作,一直都盼望着富国强兵,再也不受人欺凌。”
这段少年时代的经历对郭可信铸成一生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更加发奋读书,求学不辍,在日军频繁的空袭中,以顽强的意志出色地完成了学业。

郭可信。“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执着地追求真理”
1946年,郭可信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公费留学赴瑞典学习冶金。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优质合金钢轴承就是瑞典生产的,以致二战时盟军派遣潜水艇去瑞典偷运轴承。
郭可信顺利进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建立于1827年,是瑞典规模最大的大学,拥有上万名学生和近三千名教职工。郭可信被分配到冶金系赫尔特格林教授那里,从此进入了物理冶金领域,开始金相学的研究。金相学是研究金属与合金的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与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间的关系的学科。赫尔特格林教授作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是当时金相学的权威专家。
在异国他乡,郭可信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回忆说,“我是在山沟里油灯下念的大学,初到未受战火波及、繁荣富有的瑞典,连实验室煤气灯都不知怎么点,受到一个英国实验员的嘲笑。”这种环境反而激发了郭可信的斗志,让他更加发愤图强,立志要为中国的科学繁荣贡献一份力量。而且,郭可信“很快被金相显微镜所显示的金属微观组织结构的大千世界迷住了”,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在瑞典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成为导师身边唯一由大学支付工资的研究助教,管理奥氏体等温转变课题组。
但是,郭可信并不迷信导师。
首先,郭可信发现这位导师的研究手段比较简单:用一个十几倍的放大镜进行宏观组织结构观察,对钢厂生产出的上百个钢锭纵向刨成两半,再横向锯成若干段,这种方法也造成了极大浪费。另外,随着自己开始使用 X 射线衍射的方法研究金相,郭可信发现导师关于合金元素对奥氏体的影响的研究的某些观点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过,这位性格强势的瑞典导师绝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反驳自己。
郭可信没有盲从于权威,也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最终,他放弃了自己长达3 年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在读的学位,离开了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他回忆说,“这件事好像我是输家,工作、学位、到手的论文都完了。其实不然,我换来的是学术上的彻底解放,完全自由。”这显示出郭可信的学术态度,那就是“执着地追求真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有的精神。”
1951年,他得到了瑞典钢铁协会的资助,开始了课题——“合金钢中的碳化物”的研究。他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都在做实验,研究合金相的晶体结构。到1956年,他已经在国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当时出版的德文《合金钢手册》一书广泛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不管到哪里都要做好工作”
1956年3月,郭可信正在荷兰一座名叫代尔夫特的小城,那里的风景非常优美:运河纵横,风车牧牛,一派田园风光。然而美丽的异国风景并没能留下他。郭可信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兴奋不已,4月底就乘机经苏联回到阔别九年的祖国。与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吴文俊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一样,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自己的平生所学献给祖国和人民。
郭可信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和沈阳三地中,舍弃了繁华的京沪,来到地处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并担任金属物理室主任。
谈到自己坚持了三十一年的选择,郭可信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之所以来到金属所工作,与那里有一台仿制西门子造的苏联透射电镜不无关系。”他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家庭考虑,更多考虑的是哪里做研究、做实验的条件更好一些。
刚刚回到国内的郭可信总是穿得西装革履,与助手谈话谈到重要的问题时,往往会追问一句“懂不懂”;而对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也会坦然相告“我不懂”。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起初与金属所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但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一天晚上,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观察铝合金薄膜样品时发现,样品簿区的边缘有黑线扫动,且与电子束照射有关,工作人员以为是电子束辐照引起的位错线运动,急忙跑到郭可信家中报告。郭可信马上飞奔到了所里,经过反复观察,发现这是完整晶体因样品弯曲造成的消光轮廓,当电子束辐照时,热量造成的附加弯曲让消光轮廓改变位置。他给出的结论出来之后,在场的人无不信服。

郭可信与夫人。“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20世纪70年代初,郭可信一家“蜗居”在金属所的普通家属宿舍,晚上他只能在厨房看书写作。有一天,郭可信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东西,女儿郭桦坐在他大腿上,发现父亲的头发很长很乱,于是就悄悄给他梳头并用五颜六色的橡皮筋给郭可信扎起满头小辫。郭可信对此浑然不觉,写完稿子出门逛了一圈,直到家人哈哈大笑,他才发现自己满头的“非洲小辫”。
正是这种对学术的专注与执着,让郭可信在外界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时,都能岿然不动。而且他还把这份沉静传递给了身边团队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后期,郭可信所在的金属研究所曾一度从中国科学院划归国防科工委材料院。当时所里部分青年科技人员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怎么选择才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郭可信关注到了团队成员的思想状况,他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默默组织大家开展电子光学和电子衍射方面的学习,还把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写成笔记。他在把笔记拿给年轻人时说:“大家要学点真本事,不管到哪里都要做好工作。”就这一句话,让年轻学者们吃了定心丸,继续专注于科研。
他对所有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视同仁。姜良瑚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感慨道:“我虽不是郭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同样得到郭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从样品制备、电镜操作、图像观察和选区电子衍射谱的分析及其强度计算等诸多方面,他都给我耐心地讲解和指导,不厌其烦。郭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使我终生难忘。”
他的格局,是中国,是世界。
更难能可贵的是,郭可信虽然在研究团队内拥有权威,却从来没有在学术争论中以势压人。有一次,在一场内部讨论会上,大家对一个新晶体结构的可靠性产生了争论,郭可信也发表了看法,但并不强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意见,而是鼓励大家展开充分讨论。他的学生们回忆到:“当你有理解不了的实验结果时,不管多奇怪的问题,他都会很和蔼地和你讨论。”“在讨论会上,人人畅所欲言,个个各抒己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说些有伤他威信的话,他都从不介意,真正体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学术民主,正是郭可信的学术精神,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不变的是对学术的初心。
即使是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依然没有放弃,而是梳理编写出了一本关于金相学的史话,记录了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
“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搞上去”
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年近花甲的郭可信并没有选择“归隐江湖”,而是立志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电子显微学搞上去,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培养100名研究生。
“1980年访问中国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郭教授,那时中国才刚刚开始复苏,他正在以他超人的精力和卓越的能力指导着一大批满腔热情的青年学者。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竟如此之快地带领他的团队进入到准晶研究的最前沿。我相信他是推动中国材料科学的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位外国学者对郭可信的评价。
这位外国学者不知道的是,郭可信还在这一年立下了“军令状”。这一年,郭可信听说中国科学院进口装备处准备引进一两台电子显微镜,马上从沈阳赶到了北京,向中科院领导保证:在电镜安装后三年内拿出出色成绩。于是,郭可信为金属研究所争取到了一台当时分辨率最高、价值数十万美元的JEM200CX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安装就绪之后,郭可信立刻安排一批研究生进入实验室,那时,每到夜晚实验室总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大家三班倒,都在争分夺秒加油干。据统计,这台电镜的运转时间每年多达五千多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几乎每天都会产生新的实验结果,这也创造了历史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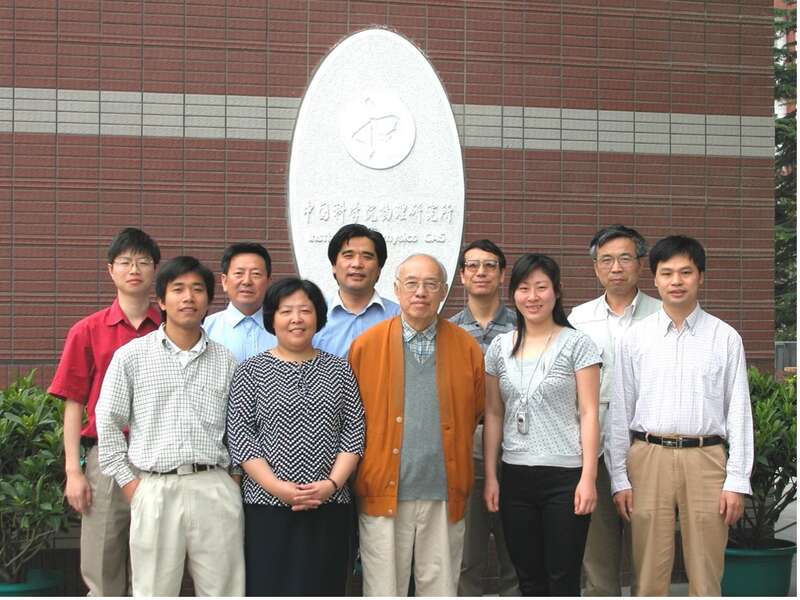
郭可信与电镜室同事。“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郭可信的学生回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忙了一夜,天已朦亮,毫无结果,人也疲惫不堪准备停机,但又不忍就此罢手无功而返,就又坚持,几经反复,终于在天大亮时找到一些新鲜结果,顿时喜出望外,所有的疲惫一下子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郭可信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亲自为金属研究所近十名19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联系了英国剑桥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瑞典隆德大学等高校的电镜实验室去进修。学生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进修机会,很快掌握了高分辨电子显微术的理论、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他们又陆续回国,成为研究所内的中坚力量。后来,金属研究所电镜组在1984年欧洲电镜会及亚太地区电镜会上发表了10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郭可信对学生的无私的爱。郭可信一生培养了119名研究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能像生产队分配工作,分配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主动性又怎能有积极性?!所以他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敢于标新立异,敢于自己闯出来。
他对学生的爱还体现在很多细节中。有学生这样回忆:“出乎我意料的是,郭先生不仅仔细地帮我修改文章,还帮我整理照片,往照片上转印图例字符。他满头白发,摘掉眼镜,神情专注、认真仔细的样子使我永生难以忘怀。他的关心使我受到莫大鼓舞,觉得有一股暖流一直暖到我心里去了。当郭先生把改好的文章还给我时我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
郭可信对学生又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学生冲洗的实验照片不够清晰,他非常生气。对沉迷于打扑克牌、荒废学业的学生,郭可信也曾经严厉批评过。郭可信一直对学界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深恶痛绝,对于一些粗制滥造、哗众取宠的论文,他告诫学生“这些人的学风品行会让国际同行看不起!”
郭可信用严管厚爱、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带出了一支学术精、学风好的科研团队。郭可信还相继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八重旋转对称、十二重旋转对称准晶等,使中国的准晶研究工作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郭可信(右一)参加电镜学会的外事活动。“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郭可信一生获得很多荣誉。他曾荣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物理奖,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获得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技术科学荣誉博士。
郭可信先生在古稀之年总结自己的人生:“回顾我这一生,在学术上只做了两件事。青年时单枪匹马地冲杀在合金钢结构的第一线,到了60岁又重整旗鼓领着一批青年人占领了准晶研究的制高点。”郭可信先生为我国的金属材料物理研究以及电子显微学研究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学生成长为相关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还包括叶恒强、张泽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十人担任各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研究员,获得国家和国际重大科技奖项的更是不胜枚举。
晚年的郭可信先生常常充满自豪地点评学生:“叶恒强又带着王大能在1983-1984年发现了五重对称电子衍射,这是突破的开始。”“张泽、王大能因发现准晶和五重旋转对称而获第一届吴健雄物理奖,王宁、陈焕因发现八重和十三重旋转对称准晶而获第二届吴健雄物理奖。他们并未因此而骄傲,得奖后也未敢稍有懈怠。”“何伦雄等发现一维准晶,李兴中最近用彩色群处理二维准晶对称,都是他们自己闯出来的。”等等。
而他的学生们则满怀对老师的深情,投入到科研事业中,正如郭可信的学生张泽院士所说,“先生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