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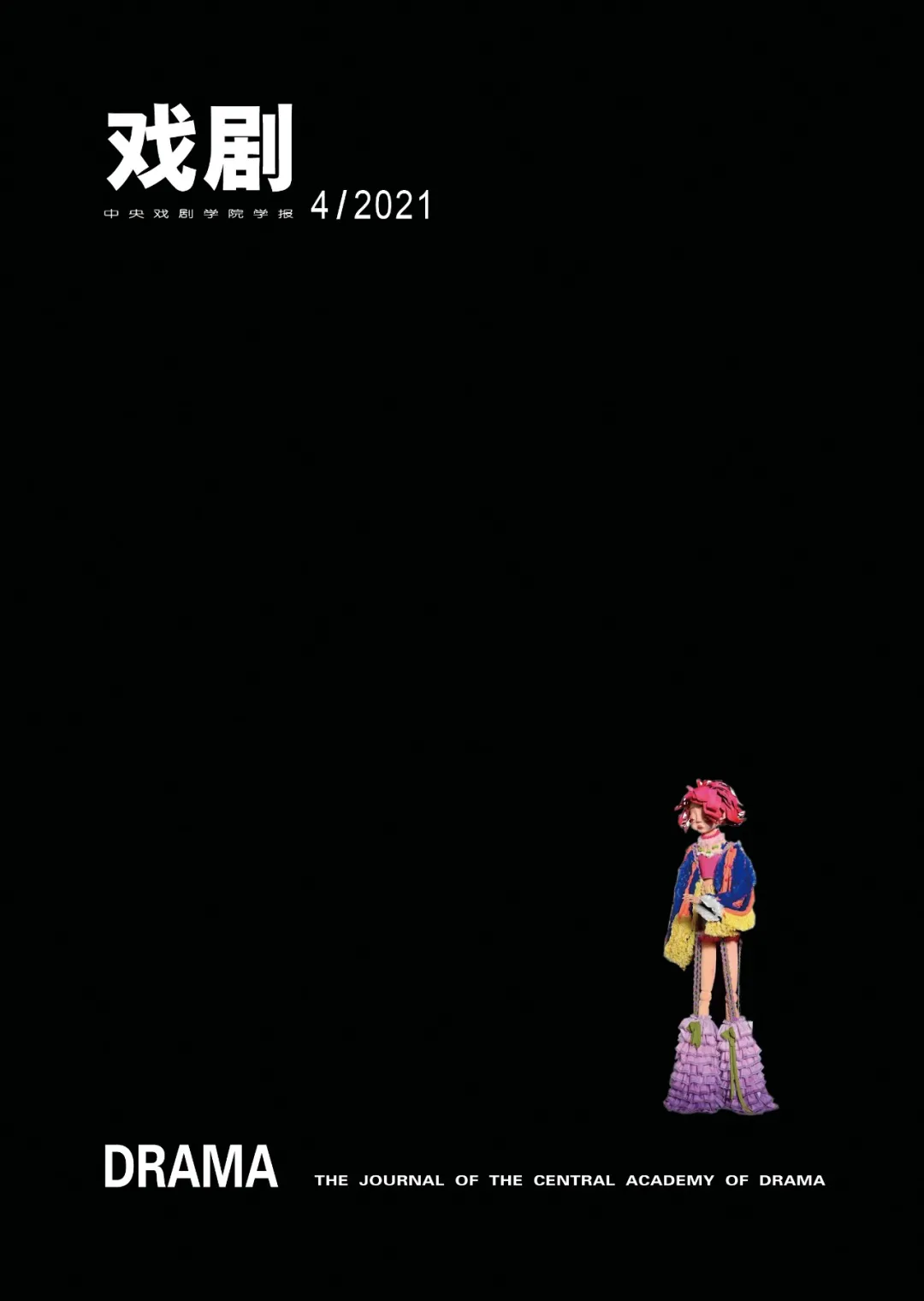
民国报刊视域下的“应节、义务戏” 之退变衰败与现代戏曲生态嬗变
吴 民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20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中国戏曲生态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乃由乡土转入都市之关键转折期。戏曲生态体系重心由乡土社会的母体文化依托,转而为都市市民社会的消闲娱乐载体,从而偏重艺术本体的精进与欣赏。戏曲艺术逐渐远离母体乡土文化,转而为精致的都市消闲商品,沦为玩赏之物。虽然梨园行有意无意地坚守文化诉求,并积极参与应节、义务戏。但“应节应景戏”“义务戏”退变衰败的事实,不可逆转。这反映了民国戏曲生态由乡土向都市嬗变的艰难,以及注定无法完成的命运。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cological pattern of Chinese opera underwent a major change, which was a critical transition period from rural to urban. In terms of the system, the focus of opera ecology is based on the maternal culture of rural society, and turns to the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needs of urban civic society, thus laying emphasis on the refine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art itself. In short, opera art has grad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become an exquisite urban leisure commodity, something to be enjoyed. Although traditional opera circle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adhere to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Festival opera and Obligation opera. However, the fact that “plays for festivals” and “plays for charities” recede into decline is irreversible. It reflects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ra ecology from rural to urba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as well as the fate that is destined to be unfulfilled.
关键词丨Keywords
民国报刊 应节应景戏 义务戏 近代戏曲生态
The pre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Festival opera, Obligation opera, Modern drama ecology
前 言
20世纪的百年,是中国戏曲生态变革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之一,而20世纪的上半叶,又是戏曲生态转变最为频繁,体系呈现最为复杂的阶段。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以新的启蒙。作为文化载体的艺术,尤其是与当时的人民最为接近的戏曲艺术,不可避免遭受影响。从旧戏批判,到戏曲改良,再到国剧运动以及后来的延安评剧改革和秧歌剧运动,戏曲艺术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几乎全过程。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忽视了戏曲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即作为艺术生态体系的自洽和生命流转。戏曲生态体系的沿革和嬗变,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体系内部的母体文化、艺术本体、艺术衍体必须与体系所处的外部生态相互适应。20世纪上半叶,戏曲生态沿革的主要路径,就是从接近母体文化的乡土观演场域进入都市。如此,以乡土为载体的戏曲生态体系,随着母体乡土文化的解构,渐次丧失了内在驱动力,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文化支撑。然而取而代之的支撑、引导性因素,并未实现文化和艺术上的双重自洽。第一,文化上,近现代中国都市,其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并未确立,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有关。大都市(如上海)早期城市文化精神,本质上依然是乡土的;第二,在艺术上,虽然都市戏曲生态,注重艺术的精进,但同时小市民趣味让原本乡土戏曲生态中被素朴乡土文化压制的媚俗、暴力、情色等非艺术的诉求得以抬头;第三,母体文化和艺术本体是互为动因的,缺失了文化凭依的都市戏曲生态,注定难以自洽和流转。由此导致都市戏曲生态的非自洽体现为:第一,乡土戏曲生态体系的局部保留,应节戏、义务戏便是一例;第二,坚守戏曲生态之特殊层面,由于体系无法自洽,于是在具体层面加以求索,如艺术本体之表演艺术的精致和雅化、流派化;第三,都市新审美诉求的抬头,但注定流于对乡土文化的背离和对戏曲艺术本体的疏远。随着乡土文化的断裂和瓦解加剧,乡土戏曲生态和艺术本体坚持,逐渐让位于所谓的都市趣味。而都市趣味本身的文化无凭依,注定无法支撑新的都市戏曲生态。换言之,戏曲生态从乡土到都市的过渡,注定失败。
民国报刊“应节、义务戏”史料,十分生动地呈现了现代戏曲生态转折过程中的挣扎和绝望。新兴都市和乡土农村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妙。城市新移民根在乡土,精神上眷恋乡土文化。然而,都市市民所受的乡土文化约束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而都市所谓的摩登现代、西化,本质上是虚空的。旧的被打破,新的未曾立,其实质,是戏曲文化生态的去内核,或者说不断抽空剥离艺术文化内涵。乡土戏曲生态被母体文化约束和压制的非艺术审美趣味,在都市戏曲生态格局有所抬头。而母体文化滋养下的艺术本体,在都市格局下逐渐瓦解。都市戏曲生态的艺术坚持,无论是文化精神上、还是本体艺术上,都不断被抽空。以至于即便是梅兰芳先生的都市演剧,都被文化启蒙者如鲁迅先生所诟病。戏曲改良,余上沅等人提出的国剧运动,等等努力,其本质,在企图弥补文化断裂带来的戏曲生态失衡。但是由于都市戏曲生态体系的非自洽,这种努力注定是极其艰难,也必然是无法彻底完成的。中国戏曲生态由乡土到都市的艰难转折和无法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戏曲生态重构,制造了万千阻力。[1](P11)
一、戏曲生态母体文化的舞台遗存
(一)戏曲生态格局与母体文化层
戏曲生态的体系格局简单而言,为母体、本体、衍体,以及外部生态环境。母体是文化源头,本体是艺术创造和接受体系,衍体是戏曲的发展性体系,环境则涵盖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母体、本体、衍体不是完全分开的,而是互为一个自洽的体系。母体和本体的交集,是文化上的诉求高于舞台诉求的戏曲剧目及演出。比如社戏、秋神报赛、傩戏,还包括一些蕴含戏剧因子的民间文化活动。此外,应节戏、义务戏,事实上也是母体与本体交集的场域之一。因此,母体文化对戏曲生态的孕育,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合理化的戏剧生发过程。20世纪以后,戏曲生态向都市转移后,仍然可以清晰看到母体乡土文化的舞台遗存。“应节应景戏”与“义务戏”便是遗存之二。
(二)“应节应景戏”与“义务戏”
民俗节庆科仪是乡土文化和儒家文明的重要体现,戏曲艺术是节庆科仪的重要载体,科仪的仪式进程本身,很多就是直接的戏曲演出或带有戏剧素朴因子的展演。成熟的戏曲艺术的源头之一,就是民俗节庆科仪。随着戏曲艺术独立品格的确立和加强,演剧和节庆之间的界限渐次明晰,但节庆演剧,却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组成。由此,“应节戏”应运而生,所谓应节,就是为了与某个节日或者某个纪念日相应和而演出。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应节戏不仅成为俗例,而且还催生了一大批特别的剧目。与纯粹的娱乐性或文人消遣性剧目不同,应节戏被附加了节庆仪式的制约。而诸如天官赐福、跳加官之类的游离于戏剧之外的特别舞台展示,则成为人们慰藉人生,祈愿祝福和礼赞的重要方式。在乡土社会,应节戏的演出场所主要在乡野路头,为集资性质的演出,与后来都市戏园子、戏馆的演出有一定差异之处。应节戏中最为一般观众熟知的是“月令承应戏”,所谓月令,就是指一年到头的每一个月都有相应的时令节庆。清代宫中逢时按节,如元旦、立春、寒食、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均要承应戏剧,这就是所谓“月令承应戏”。一年之中的节令戏本约有200多种,各节令均有相应剧本,因时轮换。戏剧内容多与民俗有关,还有粉饰太平、天朝万年之意。诚如清代昭梿撰《啸亭续录》卷一云:“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2](P56)而随着清廷的瓦解,民间梨园也开始演出应节戏,并沿革成习:
梨园俗习,每值节令,必演应节戏,以资点缀。自逊清迄,于民国肇元,仍循旧例演唱。如正月十五日之《上元夫人》,五月初五演《五毒传》《白蛇传》《混元盒》,七月初七《天河配》,七月十五《盂兰盆会》,八月中秋《天香庆节》《嫦娥奔月》。[3](P22)
从上述史料,不难发现,每一个节庆,都有对应的应节戏剧目。应节戏体现的是中国戏曲生态与母体乡土文化的血肉联系。戏曲源于民间,源于与民间民俗、乡土文化相伴随的生命情感、人生慰藉、精神信仰。艺术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价值,这一点与乡土文化高度契合。乡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民俗文化部分,关注的始终是人们鲜活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的高度缩微的体现和载体,就是节庆。而节庆的高度缩微的体现和载体,就是应节性的仪式,主要是艺术性仪式。应节戏就是其中最为鲜活的场域。因此,应节戏除了具有戏曲艺术的本体艺术特性和民俗意义外,还包含着更广泛的文化内涵。[4](P69)这种文化内涵,就是戏曲赖以滋长的母体文化源头,又是戏曲艺术本体和价值体系赖以依靠的基础。应节戏,比如春节期间的演剧风俗,具有光谱意义的准宗教信仰和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剧也在发生变化,但作为春节习俗的一部分将长期存在。[5](P28)春节应节演剧和欣赏,成为贯穿民族血脉的重要艺术线索和精神文化家园,滋养着戏曲艺术,也滋养一般民众。
(三)民国报刊应节戏史料的基本情况
进入20世纪以后,清朝土崩瓦解,乡土文化分崩离析。然而,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都市的不断兴起,应节戏顽强地留存于都市戏曲舞台,并成为都市戏曲生态异常活跃的场域之一。民国报刊关于应节戏的报道性史料,评论性文章,篇目甚多,仅以天津地区的《北洋画报》为例,便可窥见一斑。
《北洋画报》是华北报业中影响较为深远,历时较长的报刊之一。作为一份都市消闲类报纸,该报对民国的艺术生态,有较为忠实的记录和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特开辟《戏剧专刊》与《电影专刊》,是研究民国时期的影视戏剧的重要刊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透过《北洋画报·戏剧专刊》,可以整理出大量戏曲资料。这与民国各个都市的重要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新新新闻》等相仿。虽然民国报刊的戏曲史料相对驳杂,且一般性的名伶演出活动记录,京昆及地方戏,如坠子、梆子等一些地方剧种的介绍和活动记录为多。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也包含大量具有相当价值的剧评、戏曲理论、戏曲文化知识和评论等史料。比如《北洋画报》除了通过画报这一形式,刊载一般性的名家名角的便装、戏装照,还有相当的理论性、文化评述性文章。其中,《北洋画报》刊发的1587期刊物中,关于戏曲改良、戏曲舞台上重心的转移、戏曲美学、戏曲理论、戏曲表导演方面的文章数量十分惊人。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民国都市的消闲类报纸或副刊,对应节戏、义务戏的报道性史料及相关文化述评极为丰富,这些内容为我们研究民国戏曲生态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其中,仅《北洋画报》中关于应节应景戏的材料包括《明星春宴余兴戏评》[6]《明星春宴余兴戏评(下)》[7]《宜于国难期间演唱的〈挑滑竿〉》[8]《端节应景戏》[9]《上元节之应景戏》[10]《七夕应景戏之〈天河配〉》[11]《中秋节之应景戏》[12]《论应节戏》[13]。关于义务戏的资料包括:《胡碧兰举办之慈仁义务剧》[14]《寒云参加义务剧之经过》[15]《唐山妇女协会义务剧志盛》[16]《记外交后援会义务剧之始末》[17]《记北平河南中学义务剧两配角》[18]《两台赈灾戏》《记〈商报〉主办之陕灾义剧》[19]《培才义务剧》[20]《冬赈暨辽灾义务剧两夜纪》[21]《北平记者协会义务剧》[22]《北平记者会公演剧筹款之秘闻》[23]《华乐义务剧》[24]《义剧赈灾》[25]《电报局义剧》[26](P8)《谈明晚永兴赈灾会之周瑜》[27](P12)《孟小冬唱义务剧》[28]《永兴义剧杂记》[29]《酝酿中之义务剧》[30]《慈善会义务剧角色谈》[31]《慈联会冬赈义剧记》[32]《赈灾的戏》[33]《慈联冬赈义剧记》[34]。而以《北洋画报》相关史料为索引,进一步梳理民国报刊中的相关史料,则可清晰描绘民国戏曲生态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脉络。
二、都市“应节应景戏”的出现与退变
都市“应节应景戏”出现的本质原因是乡土戏曲母体文化生态的延续。换言之,都市戏曲生态实质上是不自洽、不成立的。作为都市新市民的观众,其精神文化心理,实质上是依然眷恋乡土文化。一个特别的场域,就是节庆。然而,随着都市与乡土的不断割裂,基于农耕文明和儒家宗族文化的“节”,事实上在文化上渐次消亡。这是都市“应节应景戏”退变的本质原因。由于节文化内涵的被抽空,都市“应节应景戏”名存实亡,沦为都市牟利、猎奇的手段和工具。
(一)“节”的消亡
乡土社会瓦解,乡土文化没落,农耕传统与文明被西方所谓现代文明取代。基于乡土的“节”的内涵被逐渐消解。“应节”而无节可应,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国戏曲生态演进的最重要线索就是,乡土母体文化瓦解之后,都市现代文化并未建立,至少未成为戏曲新的母体文化支撑。与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相比,我们的现代和启蒙,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精神世界,并未深刻扎根。都市市民,精神世界的根依旧脱离不了乡土眷恋。然而,随着都市与乡土的不断决裂和隔阂,乡土文化终于沦为一种空洞而虚妄的过去式。体现在应节应景戏上,就是文化信仰的要素被抽离,都市的世俗恶趣被注入。
以农历七夕应节戏《天河配》、中元节应节戏《盂兰会》为例,前者讲牛郎织女,后者演“目连救母”及“盂兰盆供奉四方恶鬼”。前者宣扬的是基于乡土的传统美德,如织女的劳作,民间谓之“乞巧”。此外还包含乡土社会以底层劳动人民为关照对象的爱情;后者则除了彰显汉传佛教的教义,还重点突出孝道这一民间伦理道德价值。此外,以盂兰盆供奉四方恶鬼,显示了我们民族互济以济世的人文关怀。这两出戏,在民间演出,十分亲民,又兼具教化和娱乐功能,是很典型的应节戏。然而进入都市以后,民国应节戏的《天河配》《盂兰盆》,往往以情色粉戏,猎奇、暴力的恶鬼,招徕观众,制造噱头。都市观众的趣味也在不断地被迎合中,越来越偏离了民族文化精神和戏曲艺术本真旨趣。
即以一般观众心理观之,观《天河配》,多着眼仙女洗澡等粉色场面;观《盂兰会》,多在意于穿插之杂耍等等。舍本逐末,至演出者站在生意经的立场上,为了迎合一般低级趣味观众之所好,乃不惜变本加厉,争奇斗胜。各以新花样胡乱参加其间,失去原剧编者之本意了。[35]
事实上,民间乡土应节戏并非拒绝民众趣味,恰恰相反,寓教于乐从来都是民间演剧的要旨。然而,这种民间趣味的张扬是有限度的,其基本限度就是要在乡土文化和人伦道德价值、集体精神信仰空间的约束之下。而真正艺术的自由,并非是“变本加厉,争奇斗胜”,而是基于文化、信仰的“闹热”“风情”“奇趣”,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的可观,迥然有别于迎合都市市民庸俗趣味的好看。其实,应节戏在清代中后期的“闹热”和“可观”基本还在戏曲艺术规定的范畴内。如端阳应节戏,斩妖除魔,舞台极为闹热而多奇观,其演剧的闹热性在清人笔记小说如《扬州画舫录》《清稗类钞》中有所体现。[36]又比如端午节的《混元盒》也是闹热、奇趣的应节之戏:
端午应节戏,则常演《龙舟竞渡》《屈原投江》诸折,然皆昆曲。后来用《封神榜》为蓝本,掺杂九妖,树立三教,命名《混元盒》。穿插固近乎臆造,而文武并重。[3]
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在中国戏曲生态的发展沿革历史进程中,民间线索事实上一直都是演剧的主流。即便是在明代中后期文人传奇鼎盛时代,戏曲演剧的主流依然在民间。这一点,往往很容易被忽视。从上述应节戏史料不难发现,清代以后的花部兴起,其实不过是民间那条潜隐的主流重新浮出水面。而雅部昆曲,不过就是民间演剧的材料之一,在民间,“昆曲衰微,乱弹兴起”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在民间应节戏的舞台,昆曲和乱弹都是材料,如何选择,具有相对的平等性。
第二,民间应节戏的演剧,十分重视闹热和可观,但并非采取后来都市剧场滥用的情色、暴力、血腥、猎奇等非艺术化的手段,而是通过文武并重的闹热场面,实现艺术上的可观和审美峰值体验。应节戏的剧目,甚至可以是连台本戏,充分满足观众的审美和文化诉求。
第三,可观的演剧呈现之上,是应节戏的文化主旨,如《混元盒》之“树立三教”,即文化内核的教化,不可偏废。换言之,一切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落脚于乡土文化和人民精神性信仰。这才是戏曲生态沿革的基本规律,也是应节应景戏的本质要求。然而,闹热可观的《混元盒》,到了民国之后,很难上演。“试问能有若此盛大戏码乎?江河日下,世事莫不如此,诚可哀也。”[3]因为戏曲生态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母体文化的松动瓦解是不争的事实,艺术本体的泥沙俱下,难以为继,外部生态的恶化,伶人与经营者的逐利,观者的猎奇,所有这一切,构成民国戏曲生态的循环恶化。而归根结底,是旧的乡土母体文化已然退出,新的母体文化并未出现,成为都市文化无法承受之重。而都市文化一旦无法真正成为新的母体文化和民众精神信仰,必然走向虚空,走向反文化、反艺术的糟粕和低级趣味。
民国时期引进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本质上没有实现民族认同,至少没能融入戏曲艺术,没有成为滋长戏曲艺术的新的文化母体。然而,即便如此,现代文明的引入,使得很多旧的文化被取缔,戏曲生态的母体结构被摧毁,此即民国应节戏发生改变原因之一:
充满一番极浓厚神权色彩,论属取缔迷信,固与今日之时代精神不符。但就各戏之艺术而言,如《捉妖》《斗法》种种,武生、武旦大开打,亦不失为几出好戏。[36]
所谓今日之时代精神,自然就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可是需要讨论的是,所谓的神权、迷信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民间的钟馗、女吊、无常这些鬼,其实都是人们对素朴的公平、正义的呼唤,并非鬼怪迷信可以一言以蔽之。若剔除所有这些文化要素,仅保留“大开打”这些“炫技炫奇”的噱头,那是十分可悲的。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所谓的迷信、封建、情色的“坏戏”被解禁恢复上演,其实就是认清了属于母体文化的“迷信”很可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民间精神诉求;同理“封建”可能是对廉政、亲民的渴求;“情色”很可能是素朴的民间风情和天然爱恋。
(二)“应”的两难
虽然说,都市戏曲生态下的应节戏陷入了文化渐次消亡、“应节”事实无节可应的尴尬境地。但无论是民间,还是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应节”的“应”的诉求,依然高涨。为了与都市的逐利和市民的恶趣相争斗,有人建议重拾文化。然而都市现代文明与乡土已然格格不入,重拾并不容易,更不可能。于是,跨越乡土文化,转而求助士子文人的雅文化,期待从传统的昆曲剧目中,寻找应节戏。以此调和都市现代文明和应节戏文化属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节戏源于乡土母体文化,与文人雅文化并不亲和。因此,当刘步云建议以《红梨记》列入“上元应节戏”[37],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甚至连一篇相关的文章和演出记录都查找不到。事实的情况是,到了民国中后期,应节戏已经举步维艰:
今年之应节戏,尤显不景气。唯荀慧生及其女弟子吴素秋,均演《白娘子》,其余大名旦班,已不见《混元盒》《乾坤斗法》。盖旧剧衰微,此亦可视为没落之一端也。[38]
不景气,成为常态。当然,应节戏不景气事实上只是旧剧衰微的一斑,母体文化没落,影响的肯定是戏曲生态的艺术本体,绝非应节戏单独一部分。应节戏剧目衰微的背后,是其文化内涵的虚空和剥离。中秋应节戏《天香庆节》,和《混元盒》等戏,早已久无人唱。[39]戏曲生态从来不拒绝新陈代谢,但民国戏曲生态的整体呈现,是畸变的,不自洽的。应节戏的衰微,是民国戏曲生态畸变的一个局部。唯一的对抗渠道,是民国大都市剧场,对表演的精微要求。然而,失去了母体依靠的表演的精微,最终沦为玩赏的精致对象。这又是另一个意义层面的“雅化”,与昆曲的“雅化”但最终落败,可资比对。“听寒外史”据此论及程砚秋,言从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十八年(1929),程砚秋七夕应节戏逐渐衰微,而程砚秋的精致化表演,并无大的裨益。
民国十二年七月初七,华乐园和声社程砚秋并未演《天河配》及其他应节戏,而将新排之《风流棒》初演之。可见彼时节,不甚重视演应节戏也。[40]
对于程砚秋而言,都市观众对表演精致化的诉求,对新戏的呼唤,让他不愿意再出演《天河配》等应节戏。他以新排的《风流棒》取代应节戏,事实上就是选择背离戏曲的文化生态母体,转而以追逐利益,迎合观众为第一要务。由此可见,即便是都市戏曲生态中最光彩夺目的名角,注定在艺术上无法实现戏曲生态体系的自觉、自洽和圆满,必然走向恶性循环的一途。而只有当程砚秋、梅兰芳这些名角成为人民艺术家,以社会主义新文化滋养戏曲生态本体,才有可能解决民国戏曲生态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后话。
而在民间,观众的选择也开始偏离母体文化诉求,比如七夕有人要求上演《小放牛》。一个带有调情意味的民间风情小戏,取代牛郎织女,显示了观众对于文化理解的弱化:
虽然唱词是描写春景,然而无伤牛郎织女的本色。载歌载舞,极富欢快以祝丰登的喜剧。[41](P24)
然而这种弱化,终究不是否定,不是彻底决裂。虽然传统节俗的教化和文化内涵被弱化,但戏曲艺术本体审美的闹热,风情得以保留。这说明即便应节已经很难,但实际上仍在艰难延续。这种《小放牛》相较于“打中台”之类应景戏,已经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持:
所谓打中台,即为满足观众之喜欢新异之心理,借梨园以外之新奇玩意,以应节应景
迎合观众猎奇心理,远离戏曲梨园本体,如此应节应景,正应节戏之末路。
三、都市“义务戏”与乡土文化关怀
如果说,“应节应景戏”是在精神信仰和生命情感层面实现乡土文化关怀,并滋养戏曲艺术,那么“义务戏”则是在现实人生的层面,实现乡土文化的特别关怀。都市“义务戏”相较“应节戏”,社会化功能更为显著。然而由于文化的渐次偏离,都市“义务戏”最终走向了退变,甚至异化。
(一)义务戏之义利之争—戏曲外界的夺利
义务戏作为常见的筹措善款的方式,在应对自然灾害、战争等国家紧急状况时,发挥了重要的民间补救作用。戏曲伶人虽然地位卑微,但在历史上,常常主动举办义务戏,甚至联合举办义务戏,让人肃然起敬。民国以后,除了一般天灾,义务戏还可以为公益事业筹款。因此许多社会组织机构通过举办义务戏来募集善款。可是,由于义务戏赖以维系其信度的传统乡土文化规定被打破,加之组织机构构成的复杂程度加剧,监管又不透明,人为的贪婪开始显露。以各种名义举办的义务戏,层出不穷,且举办义务戏还要向商户和百姓摊派相应的经济任务。最终,老百姓苦不堪言,艺人也疲于应付。义务戏的演出质量自然难以保证,乱象丛生的义务戏,沦为都市戏曲生态畸变的又一牺牲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母体文化要义的缺失,实难以行政手段加以管控。[43](P137)民间义务戏和伶人义演剧有自发性,在晚清灾荒、战乱频仍的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变迁。文化上的自觉,以及精神情感上的共情和认同,是保证义务戏成功的重要前提。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京津沪等地慈善机构和慈善家,很多都是都市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大的财阀。很难寄希望于这些组织和机构能够真正在文化上形成济世的自觉。对于不少机构和老板而言,义务戏是一桩都市生意,而且这个生意由于在文化上具有共情性的光谱凝聚力和向心力,受一般市民关注,且容易积累财富。因此,一时间资本对义务戏可谓趋之若鹜,“东也闹着演剧筹款,西也嚷着募捐演剧,这个声浪和空气,几乎充满了内地”[44](P131)。有人是盯着财富,有人则盯上了无形的社会资本,看不见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资本家财阀、官员、甚至乡绅地主,为了掌握更多社会公权,参入义务戏的组织队伍,他们试图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来获取民众支持,获取话语权,最后疯狂攫取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自身更长远的发展。[45](P36)可以想见,无论是求财,还是求名,这样组织起来的义务戏,事实上已经背离了义务戏的文化要义和初衷。义务戏功利化倾向,是民国戏曲生态畸变的缩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艺术不是沦为玩物,就是沦为敛财工具,无论身处其中的伶人、艺人如何挣扎,戏曲生态的畸变恶化不会停止,这是20世纪上半叶戏曲生态发展最大的悲哀。
(二)义务戏之义利之争—戏曲内部的争利
事实上,不仅是大资本家、财阀、官员拿义务戏开刀求财、求名,就是一般的伶人,甚至票友,也盯上了这块肥肉。如天津京剧票友,就曾积极参与义务戏演出,以彰显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其实质,居然也是求财,商业色彩日益浓重。[46](P144)伶人,名角就更是如此。一次学校的义务戏演出,奚伯啸居然狮子大开口,要价五百万,由此甚至造成了一场风波:
奚啸伯一出二进宫:非五百万元不唱!这是王久善为对付佟瑞三,不换红票“市立”玻璃被砸!某学校义务戏之风波
然而如此高昂的出场费,势必给义务戏的组织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然而义务戏的上座率向来难以保证,观众的认捐又无从预测。为了保持义务戏的演出水平和上座率,最终实现募捐的目标,请大牌成了义务戏组织者的重要手段。如此,从上到下,以利为导向,恶性循坏,义务戏积重难返。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义务戏,乃官方强制组织执行,伶人往往都选择拒绝演出,如童芷玲就因为罢演义务戏而被罚款五百元。[48](P7)行政手段催生的义务戏而为了保证敛财目的,常常以行政手段向商户和居民派发红票,即强制性地发票。
眼看又将迫近年关,眼见的义务戏当有二三十场。在如此物价高涨,生存艰难的时代,商户被派发红票,恐早不胜其扰
这样的义务戏,从上到下,毫无“义务”可言。义务戏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累赘,甚至为一般民众所厌恶。梅兰芳在南京演义务戏,观众居然高喊“退票”,这是难以想见的。当然,论其原因,一是梅兰芳要津贴太猛,而本质上,是主办方义务戏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逐利。[50](P15)利成为主导,民间所谓“小姐两张票,穷人千日粮”,概由此可见一斑。[51](P348)前面已经说到,这样的义务戏,演剧质量是无法保障的。伶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采取应付的策略。卡尔登大戏院的义务戏,名角拱卫台面,然并非“各显所长,而是徒添噱头”[52](PP10-11)。梅兰芳则逐渐放弃了《上元夫人》《嫦娥奔月》,而改唱营业剧,梅氏应节戏佳作,又成过去。[53](P7)此外,童芷玲还曾经在义务戏中演所谓的新戏《新戏迷传》。这个戏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杂烩,可以随意穿插,有点类似今天的名家大联唱。然而当时请到的名角只有童芷玲一人,于是他就只能一人应付,应付的方法就是随意唱之,姑且唱之。甚至其中还可以穿插杂耍、武艺等江湖把戏。由此可见,当时的义务戏是多么捉襟见肘,又多么尴尬,这样的义务戏可以说是令人汗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名伶在畸变的都市戏曲生态中,为了生存,也学会了变通的方法,甚至是绝活。所谓“一招鲜,吃遍天”何尝不是畸变戏曲生态之一种写照。上述义务戏,为了应付主办机构,童芷玲以“戏中串戏”的方式,高水平地完成了演出,获得了好评。然而,即便如此,成功的是演员,而义务戏,恐怕已然名存实亡。[54](P7)
虽然义务戏质量堪忧,社会号召力急剧下滑,却已然泛滥成灾。在一份政府公报中,就连一所小学新建操场,也要演义务戏筹款。这一次,票友为演出主体,效果可想而知:
指令本市私立普励小学校,据呈四月三日约听涛社票友于中和戏院演出义务夜戏一场。筹款修垫操场,添置体育器材,准予备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则备案公文传递出一个重要讯号:作为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内容的义务戏,原本完全出于自发,现在却需要由社会局备案、批准,成为一种公务事项。由此可见,乡土文化的瓦解,是义务戏衰败的根源。民国都市社会机构,虽然也承载了一定的民意,但无法在文化上让民众实现共同的精神信念。这一问题,仍然要留待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彻底解决。在民国后期的报刊史料中,义务戏的名称常常沦为“野鸡义务戏”[56](P2),闹了很多笑话。[57](P1)更为有趣的是,社会局还曾经专门发文,下令一个学校不能一年内举办两次义务戏演出。[58](P10)此外,募得款项必须严格报备,作为母体文化习俗的义务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义务戏的内涵,已经彻底被抽空。义务戏“名角虽名义上不收钱,但脑门儿费(场面和跟班的费用)委实高昂。串戏的票友不花钱过足了戏瘾,上海的难民却一个子儿都没拿到。这样的义务戏,演他干嘛?”[59](P1)最后,义务戏沦为了资本、有钱阶级、有闲阶级的盛宴,难民却一分钱都得不到,何其可笑,可悲。
四、戏曲生态母体文化的退守—乡土到都市的艰难嬗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曲母体文化在都市戏曲生态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但丧失了母体的戏曲生态依旧在艰难嬗变,担负着守护责任的,是以表演为中心的本体生态层面。
(一)戏曲生态的退守—母体退、本体守
前文已述,都市戏曲生态乃是一种畸变之发展,乡土戏曲生态则被渐次排挤出历史舞台。然而,戏曲生态是具有顽强的自我修复功能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值得特别指出。由于新的母体文化无法建构,旧的戏曲生态母体文化仍然在艰难据守,退到都市演剧的某些角落。应节应景戏,就是退守的最后阵地之一。虽然这个阵地也已经是千疮百孔,但却反映了母体文化的坚持和品格。此外,退守以外,戏曲艺术生态也在艰难实现由乡土到都市的嬗变。这一点,在应节戏、义务戏的新变化中也可略微窥见。虽然只是一点点光亮,但弥足珍贵。比如焦菊隐的复兴戏曲学校,作为义务戏的新生主体,让人精神为之振奋:
焦菊隐领导戏校校友复兴戏曲学校!十五日在艺术馆开茶话会,商演六场筹款义务戏:到王和霖、宋德珠、高王倩、沈金波等三十余人,推十一名筹委将来收回“翠明庄”为校址。[60](P1)
如果说旧科班代表的是乡土戏曲生态的教育模式,那么焦菊隐领导的戏校,让我们看到了都市戏曲生态戏曲教育的方向。而且是反映了都市戏曲生态的健康发展方向。从旧剧改良,到国剧运动、平剧改革、延安秧歌剧运动,戏曲生态一直在顽强实现自洽。然而,戏曲艺术生态的这些自我修复,由于成效、坚持等都无法撼动以角儿为中心的本质审美法则,因此,并未形成改变生态方向的潮流。戏曲母体文化的剥离,让艺术本体的表演层面顽强担负起了引领戏曲生态潮流的责任。至少在当时,保留了戏曲生态发展最为珍贵的本体艺术自足,反映了民国戏曲生态嬗变的艰难据守。童芷玲、梅兰芳等名伶,以自我修养和艺术水平,即本体生态层面的表演,努力守护戏曲生态之平衡。然而需要指出,这些名伶来自乡土。他们的艺术和人格,源自乡土文化,比如梅博士“轻财好义”,乃乡土社会文人士大夫的遗存。梅兰芳的演艺水平来自乡土艺术生态下的坐科,他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还有郝寿臣《赛太岁》,马连良《马义救主》,荀慧生《双沙河》,尚小云《战金山》,此外还有谭富英、程砚秋、侯喜瑞、李庆才、王全奎、李多奎光彩夺目。然而这份艺术之光,随着乡土社会的瓦解,已经无法通过乡土演剧,如社戏、赛社、应节应景戏反哺观众,因而也无法再获取母体文化养分。换言之,只能通过本体演艺水平的精进,获得在都市的生存:
《霸王别姬》,小楼老矣,畹华亦将息舞台生涯,日后两人的合作机会太少,杨梅之《别姬》将成绝响……杨梅演来,虽非空前,恐将后无来者了。[61](PP6-7)
这种精进,因为缺少母体文化滋养,终将成为绝唱。以今日之视角反观之,似乎已经应验。如此再去看待民国都市戏曲生态的不可能实现自洽和圆满,似乎就绝非危言耸听。
(二)都市戏曲新生态之不可能
民国都市戏曲新生态建构之不可能,可从几个方面言之:
第一,乡土文化仍在据守都市精神文化空间。以上海为例,出自乡土的剧种淮剧、越剧虽然实现了都市化,但已然保留了乡土戏曲生态的精神生命。此外,以应节戏、义务戏为例,据守都市的此类戏剧,也反映出乡土戏曲生态的顽强延续。
第二,民国都市戏曲新的母体文化无法构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也不可能催生承载人民精神信仰和生命情感的新的母体文化体系。作为戏曲生态的主体,观演双方都一方面有限坚持母体文化情思,一方面默契选择以母体文化背景下的风情、闹热、奇趣,以本体层面的精致表演作为戏曲生态的推动力。换言之,这两种选择,本质上仍然是坚持乡土戏曲生态。只是需要指出,随着都市的不断发展,这种坚持必然要经受艰难的考验。而随着乡土社会的彻底退出舞台,这种坚持本身也必然成为历史。只是,整个20世纪,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决。尤其是随着20世纪末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戏曲生态面临的文化选择更加复杂,戏曲生态无论母体文化、本体生态还是衍生生态,都越来越难以重新达到默契和融通,最终呈现出肢解的生态断层。戏曲生态事实上或许在当下已经宣告死亡,换言之,戏曲艺术或许已经进入消亡。
第三,纵观民国乃至整个20世纪,母体营养的缺失,小戏运动的终止,戏曲的新生态事实上已经完全停止萌芽。戏曲生态的生命在母体文化,这是一切表演和演出内容的源头。如果失去了这个生命源头,一切的演绎都难以为继,或者沦为空洞的技巧。而没有文化生命的支撑,演员的艺术生命也难以坚持。毕竟演戏本身极为严苛和艰苦,必须要文化的滋润,以及同在文化层的观者的激赏,才能支持艺术的前进。这一点,在20世纪的后半叶,依然没能得到充分地重视,殊为可惜。
义务戏、应节应景戏,在由乡土到都市的过程中,艰难适应,但最终,难免落败的命运,因为都市戏曲生态最终放弃了承载“应节戏、义务戏”的母体文化。义务戏承载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关怀,是对社会制度和行政政策的一种民间补充。在民间乡土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完整健全的时代,节俗的教化、生命情感的慰藉、精神价值的信仰,在准宗教意义的应节戏之闹热、风情、奇趣的艺术世界中,得以彰显,淋漓尽致。民众的狂欢和宣泄成为一种人生的重要补充和能量来源。然而,都市戏曲生态下,这一切的文化默契被打破,共有的文化价值体系被打破,艺术的核心价值成为供人玩赏的标的物,失去了生命意义上,生态意义上的体系化生长能力,这就是论断民国都市戏曲生态重构绝不可能的重要前提。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本来可以成为新的母体文化源头,然而却没有被充分挖掘。导致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戏和新编戏,并未在生态重构上实现自足。[62](P14)而基于原来的乡土母体文化的传统戏,则由于新的母体的出现左右彷徨。其中最鲜明的例证,就是作为传统母体文化生态要素的诸多因子,在1949年后仍然一再被否定为“迷信、情色、暴力”,这是值得深思的。因为前文已经说到,这些被批判要素是民国抛弃母体后造成的,并非源于母体。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又是多么地艰难
参考文献
[1]吴民.戏曲生态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方向[J].戏剧文学,2013(06).
[2]晓然.什么叫应节戏[J].中国工会财会,2014(02).
[3]松生.端午应节戏:漫话八本混元盒[J].三六九画报,1943(12).
[4]李楠,陈琛.论应节戏的文化内涵[J].节日研究,2011(02).
[5]彭恒礼.春节的演剧风俗[J].节日研究,2011(02).
[6]明星春宴余兴戏评[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86期,专刊第11期,1928-05-09(01).
[7]明星春宴余兴戏评(下)[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88期,专刊第12期,1928-05-16(01).
[8]宜于国难期间演唱的《挑滑竿》[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920期,专刊第206期,1933-04-15(01).
[9]端节应景戏[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102期,专刊第264期,1934-06-16(01).
[10]上元节之应景戏[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206期,专刊第297期,1935-02-16(01).
[11]七夕应景戏之《天河配》[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278期,专刊第320期,1935-08-03(01).
[12]中秋节之应景戏[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296期,专刊第326期,1935-09-14(01).
[13]论应节戏[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1511期,专刊第397期,1937-01-30(01).
[14]胡碧兰举办之慈仁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338期,专刊第58期,1929-06-29(01).
[15]寒云参加义务剧之经过[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377期,专刊第70期,1929-09-28(01).
[16]唐山妇女协会义务剧志盛[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400期,专刊第77期,1929-11-21(01).
[17]记外交后援会义务剧之始末[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401期,专刊第78期,1929-11-23(01).
[18]记北平河南中学义务剧两配角[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421期,专刊第85期,1930-01-09(01).
[19]记《商报》主办之陕灾义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479期,专刊第102期,1930-05-31(01).
[20]培才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491期,专刊第105期,1930-06-28(01).
[21]冬赈暨辽灾义务剧两夜纪[N].北洋画报1戏剧专刊,总第551期,专刊第123期,1930-11-15(01).
[22]北平记者协会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652期,专刊第152期,1931-07-18(01).
[23]北平记者会公演剧筹款之秘闻[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55期,专刊第153期,1931-07-01(01).
[24]华乐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58期,专刊第154期,1931-08-01(01).
[25]义剧赈灾[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70期,专刊第158期,1931-09-08(01).
[26]电报局义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74期,专刊第159期,1931(09).
[27]谈明晚永兴赈灾会之周瑜 [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66期,专刊第150期,1930(09).
[28]孟小冬唱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76期,专刊第160期,1931-09-12(01).
[29]永兴义剧杂记[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676期,专刊第160期,1931-09-12(01).
[30]酝酿中之义务剧[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192期,专刊第292期,1935-01-12(01).
[31]慈善会义务剧角色谈[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195期,专刊第293期,1935-01-09(01).
[32]慈联会冬赈义剧记 [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198期,专刊第294期,1935-01-26(01).
[33]赈灾的戏 [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296期,专刊第326期,1935-09-14(01).
[34]慈联冬赈义剧记[N].北洋画报·戏剧专刊,总第 1341期,专刊第341期,1935-12-28(01).
[35]“天河配”与“盂兰会”,旧七月里两出应景戏[N].民治周刊,1947-05-10(01).
[36]端阳节应景戏均带有斩除妖怪色彩[N].民治周刊,1948-03-05(01).
[37]刘步堂.红梨记宜纳入上元应节戏[N].新民报半月刊,1941-05-07(04).
[38]今年应节戏不甚景气[N].三六九画报,1942-05-22(01).
[39]砚斋.今日中秋梨园应节戏[N].中华周报,1944-02-20(02).
[40]菊生.程砚秋演《天河配》[N].立言画刊,1923-04-06(2).
[41]王伯龙老郎.秋之特号:七夕应景戏,宜演小放牛[J].立言画刊,1941(152).
[42]戏剧论坛灯节应景戏:多藉“打中台”号召[J].游艺画刊,1942(05).
[43]王兴昀.义务戏中的戏曲艺人和主办方—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考察(1912—1937)[J].戏剧文学,2019(02).
[44]郭常英.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J].清史研究,2018(04).
[45]周淑红.清末民初上海的义务戏演出[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46]王兴昀.民国天津京剧票友、票房探析(1912-1937)[J].戏剧文学,2015(11).
[47]奚啸伯一出二进宫:非五百万元不唱!这是王久善为对付佟瑞三,不换红票“市立”玻璃被砸!某学校义务戏之风波![J].戏世界,1947(349).
[48]怀玉.江南艺訉药业巨商义务戏:五花洞节外生枝,潘金莲罚款五百,童芷苓小姐得了一个教训(附照片)[J].游艺画刊,1943(02).
[49]再会吧上海:白玉薇乘轮赴汉,慈母黯然回北平、天津义务戏连续不断,派销红票不胜其烦[J].一四七画报,1946(02).
[50]梅郎在京风头十足:买不到票屡闯穷祸,义务戏要津贴太狠,末晚唱黑戏喊退票[J].影与戏 ,1937(13).
[51]谭富英后半期义务戏里,王蕙蘅六百万过瘾记:小姐票两场穷人千日粮(附照片)[J].戏世界,1947(348).
[52]绍萧救灾会义务戏之我见忆华[J].十日戏剧,1939(33).
[53]聊公秋节剧谈:旧剧词句颇多点缀秋节者,应节戏亦有新陈代谢之概[J].游艺画刊,1941(05).
[54]童芷苓留神!大义务中演新戏迷传,主管当局派人去调查:唱的完全戏中串戏没有出现规矩的地方[J]. 一四七画报,1948(07).
[55]社会局命令:指令本市私立普励小学校据呈四月三日约听涛社票友在中和戏院演唱义务夜戏一场筹款垫操场添置体育器械各节准予备案由[J].北平市市政公报,1937(401).
[56]野鸡义务戏[J].天津商报图画半周刊,1931(11).
[57]义务戏之笑话—不票[J].天津商报画刊,1932(14).
[58]教育、命令、指令私立玉杰民众女子职业学校_呈报补演义务夜戏由[J].北平特别市市政公报,1930(31).
[59]义务戏演他干吗?多事[J].天津商报画刊,1932(06).
[60]焦菊隐领导戏校校友复兴戏曲学校[J].戏世界,1947(336).
[61]弭鞠田.追述记北平看警察医院义务戏,杨梅合演“别姬”,为不可磨灭之一夕欢[J].十日戏剧,1937(12).
[62]吴民.拿什么拯救你—20世纪戏曲的两次重大变革及其对当下的启示[J].戏剧文学,2013(11).
[63]吴民.政治禁演与民间风情的悖谬—建国初期“坏戏”艺术趣味重估[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5(03).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