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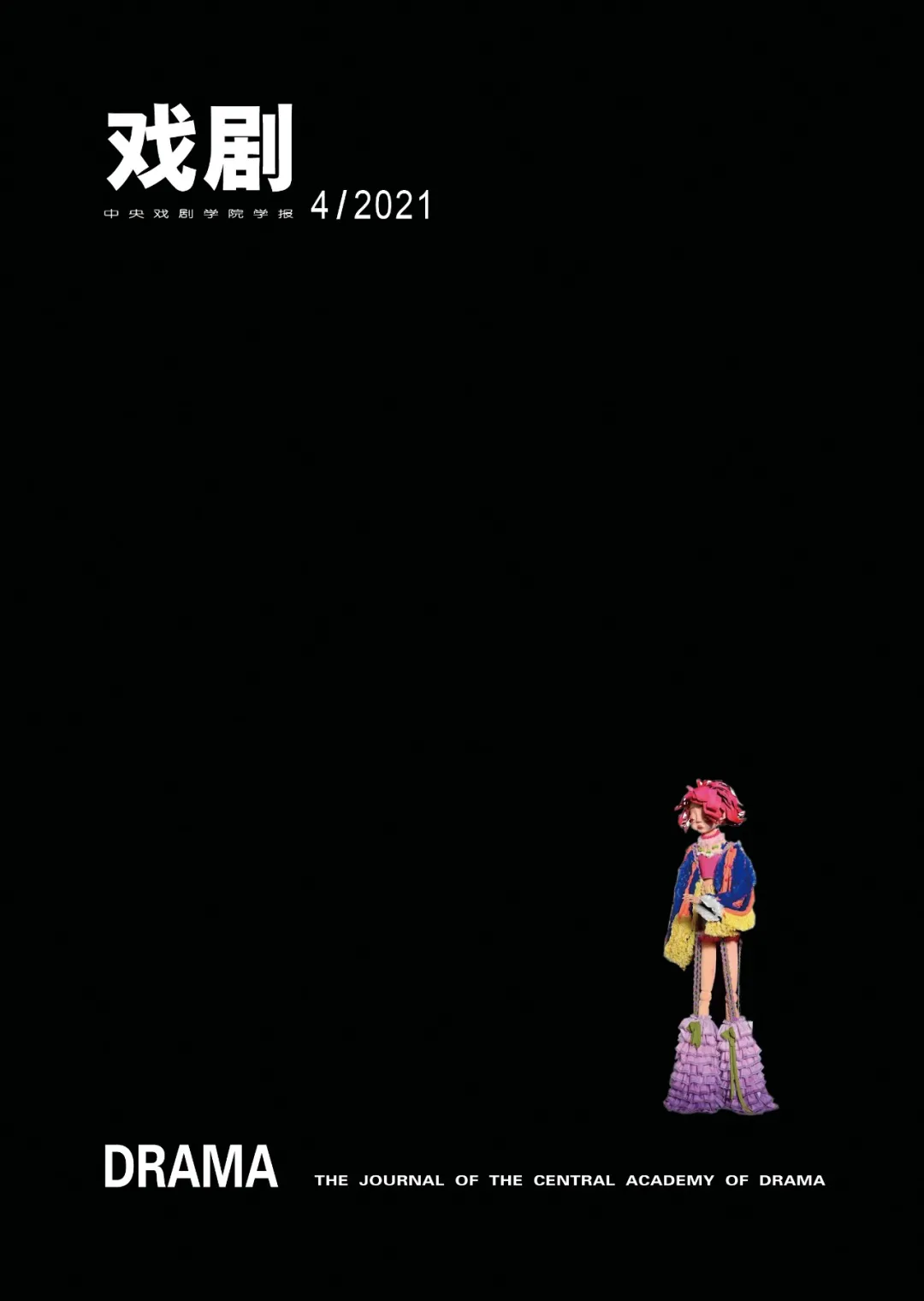
识别下方二维码查阅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电子版

算法时代的“直言剧场”
——论文慧生活舞蹈工作室作品
王音洁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丨Abstract
本文聚焦于中国编舞家、剧场艺术家文慧及她的生活舞蹈工作室1994年至今的创作,涵盖了“直言剧场”、后女性主义的性别行动、新的主体建构和媒介时代下的“直言”,从这几个维度深刻阐释了文慧的创作和当下时代的关系。文章的分析涉及她的剧场语言、身体运用和主体重建,以及她的编舞手法,通过这几个丰富层面的梳理,论证文慧的创作作为当代国内剧场不可或缺的存在,解析她作品里的批判性和她介入并建构剧场共同体的力量。文章最后谈论媒介时代的“直言”和保证“直言”的权利在当代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剧场与社会剧场如何在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作中融汇于一体。文慧持之以恒地开创了算法时代新的艺术伦理法则,使剧场成为人类世的逆熵联合体所在。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ritically acclaimed productions of famed Chinese choreographer and theatre artist Wen Hui and her living dance studio, covering the parrhesia theater, gender action from post-feminism, new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parrhesiastes in the media age. Arguing for the existence of Wen Hui as an indispensable Chinese contemporary theater, The paper examines Wen Hui's dance theatre style, contemporary movement and subjectile, her choreography style,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in her choreography , her prowess in collaborating and building a thriving theater community in China, and the pivotal role she plays in ensuring the right of parrhesia in public sphere. Wen Hui and her living dance studio have clearly created new art ethics values and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art theatre with social theatre in the algorithmic era. She makes theater become the negentripic combin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
关键词丨Keywords
直言 公共领域 性别 后女性主义 基底 伦理 逆熵联合
Parrhesia, Public sphere, Gender, Post-feminism, Subjectile, Ethos, Negentripic combination
2021年5月26日,德国歌德学院宣布,本年度“歌德奖章”(Goethe-Medaille)授予全世界三位艺术家,其中有中国的剧场艺术家兼编舞家文慧。上一次得到这个殊荣的是诗人、翻译家冯至,在1983年。中国的得奖者从男性到女性,从文学翻译到当代剧场艺术,这里面的变化,是时代的跨度,也是时代的刻度。
文慧是谁?当这个得奖消息在国内传开时,引发许多人的问号。作为一个长年耕耘于肢体剧场,使用身体元素作为言说本体的艺术家,的确不够大众。但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文慧又是个从未缺席过的当代中国见证人,一个当代中国公共空间内的“直言者”(parrhesiastes)。
一、“直言剧场”
此处用到“直言者”这个词,是一个来自于古希腊的名词,意思很简单,说真话的人。但其后面却不止是这么简单。怎样才算是直接地言说?在历史的演变中,它有它内在的深意。
福柯在他的生命的晚期,连开几次讲座专门谈论这个他视为是自我技术的话题。在他的论述里,“直言”(parrhēsia, παραρσία)虽然是直接说话,但绝不是喋喋不休,“直言者”不仅真诚地说出他的想法,而且他所说的还是真理,是信念和真理的完全一致[1](P291)。
福柯接着在他有关“直言”的演讲里归纳“直言”的五个特征:坦率、真理、危险、批判、责任,也即:坦诚说话,说真理,带着危险和冒犯说,提出了对他者的批判,带着说真理的责任感来说话。
那么文慧作为一个剧场艺术家,一个编舞家,一个纪录片导演,她的创作又是怎么和“直言”牵扯的呢?
文慧和她的生活舞蹈工作室(Living Dance Studio)是由她和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一起于1994年在北京创立。创立之初,就活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和国际最具探索性的艺术场域里。比如1994年工作室的第一个作品《100个动词》,文慧从“人只要活着,就是一个个动词”这句话出发,找来10位非舞者的朋友一起完成作品。她设定几个基本的动作,同时将每个人的日常动作交给他们自主决定完成。表演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舞蹈教室里进行,从搭建舞台时就开始了。表演的动作有日常生活的,也有逾越日常框架的。每个表演者都用一种亲密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不是自身的陌生对象,而是解放的途径和自由表达的符号。此后工作室的创作迅速推进着。1999年,推出《生育报告》。实际上从1995年开始,文慧就在采访身边的女性,发现生育体验是了解女性世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于是在1995-1999年间,她深入采访了几十名27-93岁的女性,把她们的现实经历,和几位舞者的切身经历,那些来自田野调研和社会观察的素材,以及舞者的口述,舞蹈的语言,舞台空间的调度,实时影像采访的介入,统统融汇于其中。身体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被激发、调动,被挖掘,是一个表达情感、认识自身的媒介,而不仅仅是符号化的载体了。这一点和第一部作品比有很大的不同,也和当时中国艺术圈开始流行的行为艺术表演的身体使用很不同。进入2000年,艺术家敏感于城市化的脚步甚嚣尘上,奥运场馆建设、土地买卖、房产开发带来大量外来务工人口,从她居住的北京更是强烈感觉到这些人的身体在空间里的存在。于是在2001年,文慧与另外3位艺术家(宋冬、尹秀珍、吴文光)一起邀请到30位在京民工,经过一段时间(8天)的排练,在一个准备改建的20世纪80年代老厂房里,和舞者一起完成了《和民工跳舞》。这个作品出发点是表现资本大开发下的廉价劳动力,以民工的身体为材料,打磨、激发、搭建、叙事、发声,将在资本的尘土中湮灭的劳动者凸显出来,令他们清晰可识别,因而能够被承认。在处理与受邀表演者-外来民工群体关系时,首先是付给他们和打工同样的费用;其次在排练中,编舞文慧总是以观察者的方式捕捉他们的肢体习惯、劳作痕迹,然后就地起舞,赋值于其上。其中有一段演员哼起家乡小调,那就是他们在做工时的放松方式。文慧将它编织进新的织体,给予整体新的节奏。新世纪之初,在中国房地产开发资本大发展的第一声号角里,在那个改变当代中国城市图景的前夜,艺术家敏锐存像。2005年工作室创作根据2003年的“非典”记忆而做的《37°8报告》,将公共疫情的记忆在剧场里展现出来。7位舞者的连接互动是通过身体的挤压而不是敞开达到,这些肢体动作投射出来的情绪,就不止步于疫情的反应了,而是现代人普遍恐惧、孤独、虚弱的精神状态,是加缪意义上的荒谬。2011年文慧集结北京草场地工作站的5位纪录片拍摄者,以大家参与的“民间记忆计划”(回老家村庄拍摄1959-1961年人们的饥饿记忆)为线索,结合身体语言,创作了《记忆在路上》,糅合转化在剧场空间里。2015年,文慧和几位伙伴一起完成了《红》,把对《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情况和相关文献、年代记忆的追溯,与舞者的现场表演,舞者的个人记忆,这些维度的材料互文编织。作品以《红色娘子军》为切口,内容涵盖了过往岁月对身体的规训印记、父权秩序下女性的压迫感、威权空间里分裂的身体意识……,呈现当代中国个人身体的规训和个人主体的建立之间的掰扯,以每个人的身体作为考察的田野,编年记载的材料,做了一次多维度的剖析。
以上提到的几部作品,都早早跨越出戏剧作品这个概念。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在国内正规的剧院内上演过,而是它们连接的话题,它们面对的问题,它们表达的言说,它们引发的讨论,都把观众变成了公众。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当下的活人在那些经历过的共同时刻里,我们自身社群热题的再现转化: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剧场为框架转译了出来,成为一个可观可论可转帖可点赞的界面。这个界面的出现首先仰赖艺术家能够坦率讲出自己想说的话,而且她所说的话带有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反省,她说这些话本身,亦自带了一份想说的责任,以及风险,未知的,也许是冒犯的风险。也正因为此,这些剧场作品,使我们看到了观众作为公众,同时公众作为公共领域这之间的扣合关系。讲的是与每个人相关的生活经验里的生命体验,具有那种切身性,使每一位观众难逃伦理的追问,这是直言的剧场,是勇敢者游戏。
在“歌德奖章”的获奖理由上这样写道:
文慧属于中国舞蹈剧场的先锋人物,她的编舞作品融入了纪录片元素和中国日常生活主题。她尤为关心历史在人们身体中所留下的痕迹,致力于将身体打造成“反思档案馆”。她的作品往往扎根当地,但其舞蹈形式却受到世界各地思想的启发。她代表着中国独立而富有创造性的自由艺术界。这既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讲述了主流叙事之外形形色色的日常故事。

2021年8月28日德国时间11时(北京时间17时),2021年“歌德奖章”颁奖典礼线上举行。中国编舞家、舞蹈家文慧从歌德学院主席卡罗拉·兰茨手中接过奖章。此前一天,文慧剧场新作《我60》于当地时间8月27日19时在魏玛艺术节上全球首演。
日常的故事,这是我们编织当代中国叙事所必须的经纬线。一个宏大的中国梦,是由无数这样的个体之梦融汇而成。文慧和她的舞蹈工作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提供了新叙事的意识和结构,那是一个不再被欺压,自主自强且逐渐富有之后,需要抛开过往历史的重压和遗留的旧诗体,用鲜活的当代句法一个字一个词再去锻造的中国叙事,不仅仅停留在“受苦受难”里的中国叙事。那里面有富足后的欢歌,也有舍弃掉的旧宅,那里面有我们每一个人过去不久的时光。
前文提到的作品,是文慧的创作里比较主要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如个人的情感、记忆、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点等,她同样以足具分量的作品作出回应。尤其对于女性的命运,女性的成长,性别与身份和对性别身份的跨越,她仍然在推进她的思考与表达。她积极地将剧场作品,特别是舞蹈剧场作品,脱开审美表达的封闭框架,进入到公共领域,进入个人真实的生活叙事中。每一次创作,文慧都试图以身体为出发点,去激发表演带来的可能的动能,以感性的现实间接暗示出缺席的对象(真理)。剧场的表演始终是一个属于情感张力的场域,它产生认知,更带来各式各样的欲望与情感反应。文慧使这些张力溢出观众席,让观众带着剧场的那份温热走向自己的生活,直面真实,抛弃我们面对自我处境时的自封、自闭、自毁。说话不是行动,但言说是行动,“直言者”就是行动者。在文慧的剧场里,世界的舞台撞上了剧场的舞台,它不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是日常生活里发动关切的能力问题,这就是“直言剧场”,它带来了信念。
二、作为行动的“性别”:后女性主义的书写
虽然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不乏影像和言说,但肢体肯定是第一位的创作语言。而作为一位舞蹈家,带着性别的身体,作为性别符号来使用的身体,更容易被无论艺术家还是观众还是评论界预设为其先行的路径。在文慧的作品中,她是怎么面对这个危险的裹着红利的形而上设定的呢?我的意思并非认为“女性”这个符号不好,需要我们辨析和考察的永远是符号成立的原因和对它的使用。
在生活舞蹈工作室作品里,直接与“女性”身份相关的作品有《裙子》(1996)、《生育报告》(1999)、《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2012)、《红》(2015)和新的作品《我60》(2021)等,这个直接不光是主题,还包括表演者,也都是女性。




最新的作品《我60》
《裙子》作为早期作品,来得最直接。它源自文慧与一条过长裙袍的关系,从某天不停拎起过长裙角的动作里,她把女孩与最具性别符号的“裙子”的关系发展开去。在这个作品里,文慧显示出对女孩身份的“寻思”“打量”。《生育报告》则跨出了一大步。虽然着眼点在于女人生孩子,关于女性的生育体验。但是正如她说的,“一个舞者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学到的舞蹈动作在这里只有消失。”这是一个关乎从“女性”性别出发的行动,而不是彰显女性身份的作品。这里面有具体的生育故事,也有流产故事,有溺毙的女婴,有育儿,是一整条生育线上的故事。对这些枝蔓的全部展开,才是这个生育故事的重点。文化上特定的认识体系先验地建立了男、女这种“生理性别”,演戏的过程就是操演(perform)这个性别身份的过程。操演的重中之重,是那个我们认为的最理所当然的点—“生殖功能”。所以整个舞台也是用很具有中国20世纪60-80年代感的“喜鹊梅花”床单铺底,不时还散落几床棉胎;不时,又变形出几个折叠的木床架。4位舞者有一位主要负责言说(她也是真有生产经验的女性),另三位主要负责肢体。戏从女人噼里啪啦的絮叨开始,随即伴着倾盆的瓜子,拉呱声四起,除了琐屑还是琐屑。这是多么实在和“稳固”的表象认知符号,这是我们盲目而热衷表演着的日常舞蹈动作里放大的日常:打扫、装扮、床笫、翻脸、风言风语,和一次一次落在这种“女”体上的生育任务,它们一起构造出一个持久不变的性别化自我“假象”,嵌落在社会的主流结构中。经年累月,这些不断重复的程式化生活建构着“女人”,似乎天衣无缝。但也就是在这里,性别显示出它的脆弱来。脆弱感尤其显露在吴文光作为男性符号,拿着摄像机闯入舞台,把4位女演员一个一个逼入后台小屋。房内拍摄的女演员脸部特写即时投影于舞台的大屏幕。这个男性来展演的记录者(闯入者),将一种被社会空间给予的角色配置裸露给观众,观众感到莫名的暴力压迫感,它来自于理所当然的特权和服从。剧场空间里的重复,是对日常程式的重新演绎,更是带领大家重新经验,重新经验已经牢固建立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舞蹈工作室把性别当作了行动,而不是表演的理由,不是表现本身。
这一行动是公共的行动,它一路贯穿下去,继续绽开在《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里。2011年文慧回云南老家拍摄,偶然得知家族里的亲戚,84岁的“三奶奶”,于是就将她的故事拍了下来,讲述三奶奶12岁嫁人,14岁产子,20岁离婚,土改、“文革”……,安居于云南某处山村里的故事。拍完后文慧以此做了纪录剧场作品,并和自己的母亲和另一年轻的女演员小银共同完成了该剧。究其一生,三奶奶似乎是恪尽职守扮演了一位女性长者、母亲,然后她早早离开感情不合的丈夫,受着动荡时局的冲击,却依然头脑清明,与文慧一起讲述往事,一起舞动、嬉闹。她爽朗、天真、勤力、敞开,自始至终未被任何主流话语收编而成就独一的生命状态。[2](P31)这个剧场作品正是专注于展现这种状态,无意中以“三奶奶”为路径越过了“性别”的建制—展现的是天地间一个生命的位置,而非女人的生活。这个位置是创造生命的原始力—“盖娅”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能看到创造,看到毁灭,看到秩序。黑暗和混乱交织在生命的希望里。在这个位置上,性别规范是幻影,性别是行动的开机密码,踏着生的每一步节律,带领我们走出新的维度。2015年的《红》正是站立在这个新的维度上。这一次文慧直接在身体上制作档案了。“从2008年开始,我一直在研究身体记忆,就是身体怎么样联系到社会和历史。后来我跟国外的一些艺术家也谈过关于身体记忆的问题。这个身体记忆,包括跟你的上一辈,再上一辈,爷爷奶奶,他们的历史,和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都有关系,都是关联的。这是为什么我想做《红》,《红》是“文革”期间关于我成长的环境。在这个记录剧场里,四个表演者都是以她们的真实身份参与,呈现她们对那段历史的身体记忆。”
一位当年参演《红色娘子军》的女士给观众展示这个舞蹈对她肢体的规训,一位从小习舞的女生展示本土舞蹈教育对她肢体的规范,一位乡村女孩展示底层生活给她肢体形态留下的印记,她们边舞动边讲解,舞台就像充满了注释的文档,并穿插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教程示范书—通过这个操演过程,我们见证了身体表现和生产文化意义的方式,见证了一整套身体语言编织铸就的过程,替长久以来身体上的烙印和伤口追问我们身体的全部情况。一个秘密跃然台上:没有先在的身体语言,那么也就没有先在的身体性别身份了。“真实的性别身份只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3](P185),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红》这个作品要呈现的,不光是真实的性别身份的虚构性,还是每一个人的身体被操演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如此隐匿,要寻找到窥探它的可能性都大费周章,有赖艺术家用直接有效的形式手法进入、打开。文慧站在了新的维度起底性别,谈论身份,这个新的维度是—不将性别作为先设的符号。砸碎那个旧锁链,不一定迎来一个新世界,但至少可撼动旧世界的法则。“性别既不会是正确的,也不会是错误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表象的;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后天获得的。然而,作为那些属性的可信的承载者,性别也可以变得完全、彻底地不可信。”[3](P185)新的维度是抛开性别设定的后女性主义书写,因为走到今天的女性主义,最应该面对的,无疑是如何跨越权力辩争、跨越身份法则、跨越以普遍性替代世间法去谈问题的压迫性愿望,获得推动实践的思想资源这个难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的框架依然有效,如果性别作为行动依然有效的话。
三、洞穿:在“基底”(Subjectile)上舞动
4位舞者,4个身体,被政治舞蹈收编的身体、被制式化舞蹈规训的身体、被社会阶层压制的身体、批注着文本的身体(请注意,这里的“批注”完全是在中国古籍的批注本意义上使用,批注人虽以文本为二手创作,但亦时刻兴发,与现代文论的注释不同)。她们和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影像资料一起,铺满1小时21分时长的舞蹈剧场作品《红》。文慧这样编排这个作品:曾经的样板戏演员讲解一个个标准动作的炼成;年青的舞蹈学员告诉观众什么是舞台的8点位;辍学的农村女孩讲述失学和丧父在自己身体上的印记;批注者来回穿梭,披沥其间,不仅帮忙阐发,还会动心现身,借题发挥,幽默注解。3位对着观众的告白者展示的是身体被器官肢解分隔的过程(在阿尔托认为,器官组织是关节扣连,是功能和肢体的连接,这个组织既构成我们自身的四肢又将其分隔。关节连接是身体的结构,而结构又总是被抽离自身的结构。身体如分成器官,血肉之躯的内在差异就敞开了一个缺陷。由于它,身体在将自己当成精神并自认作精神同时向自身阙如[4](P339)),而批注的帮闲者就正是阿尔托认为的“无器官的身体”的存在,一个未被分层的身体。它的作用是重建,将血肉之躯还给人,使肢解身体的器官装置关闭。无器官的身体带动着舞台上的重组工作,给重组标出节律。它就是德勒兹(Deleuze)谈及《戏剧化的普遍性》所说的肉身承负理念的“幼体”[5](P371),在身体还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概念表象之时,它承受着运行的流线,滑动、旋转。批注者的肢体是拙的,无能指的,靠近潜能的,有时像讲述者的梦,有时是被打码的对象,有时是口中之物,有时则是思维本身。
一个艺术创作,仅仅只是找出欲望并把它们暴露给公众,那是不够的,网络小报足以胜任。能够成为作品,就在于通过艺术语言本身来建构起关于自身的真理。这仰赖于艺术语言的操演力量。这个过程中,演员是牺牲者,她们一边讲述自己的经历,一边驱逐着自己,献祭了自己。她们把自己献给什么呢?以文慧的创作来看,是交付给了一个敞开的、可以无限阐释的疆域,是朝向自我重塑开放的努力。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自救”。自救暗示着有个自我的实体。福柯首先反对的就是这个,他说自我是“每个人自己和自己建立的关系类型”。但这种和自我保持的关系不是一种身份关系,而是“差异化、创造和革新的关系”[6](PP104-114)。
舞蹈剧场的空间里,几乎是践行这个观点的最佳场所。直接的言说表达,容易带来一个很难摆脱的困境,即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里认为的,也是朱迪斯·巴勒特在《消解性别》里辨析的:直接的告白,是让我们逐步被权威话语所控制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讲述需要我们遭受的压抑和迫害,比如“性受到了压抑的唯一理由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它堂而皇之地说出来”[7](P166)。因此从这个点出发,“直言”之“言”,就不仅是言辞之说了,它还是肢体之说、衣衫之说、眼泪之说、尘土之说……,“言”也在非语言的表达因素里。这亦是阿尔托强调的重点,当他夸赞“巴厘岛剧场”时,他提到这种一切在舞台空间中勾勒,在四肢和空气以及一些叫喊、色彩和动作之间浮现的纯粹剧场,它创造一种在空间运作的动作语言,“在空中、在空间里,从视觉和听觉上,组成一种具体可触的、活泼的细语。不消一会儿,我们就神奇地与它认同—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在说话”[8](P75)。这是阿尔托的戏剧思想,倚重脱离剧场的运动,倚重思想与肉身须臾不分离—“对我来说,有思想就意味着维持思想,回应自身。思绝不只意味着气未断绝,而是时刻与自身重聚,在其自身内部的存在中,不曾有一刻停止感受自身,意味着从自身到自身的连续在场,一种思考自身、把握自身、认识自身的思想的永久汇集,是一种神圣逻各斯的再现。人从未停止对它的怀念”[9](P417),这就是阿尔托意谓的血肉之躯的形而上学,是不曾被盗窃的,不被文本和词的剧场劫掠的那个“残酷剧场”。
“身体是意义逃逸的所在。舞蹈的艺术,是在身体里捕捉运动的流逝,同时赋予它意义,为那些不断流失、不断逃脱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编舞家和舞者的工作,就是在意义的逃逸里捉住、留住意义,在运动的流逝里用运动创造意义。” [10](P22)法国编舞家玛蒂德·莫尼叶(Mathilde Monnier)在与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对话时这样说。面对把自己当作媒介的境遇,舞蹈有机会和自我产生直接的联系,这是别的创作方式不曾有的力量。这种不与自己分离的力量,来自对主体的认知。但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早已陷入了危机。自马克思、尼采以来,现代主体开始受到不断地质疑和批判。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我们还能怎样去谈论主体呢?在后现代“解构”哲学家德里达看来,阿尔托晚期有关素描的思想中,重新激活了主体概念,阿尔托用的词是subjectile,有基底,显形的地方的意思,也有学者译为“支撑基底”[11](PP72-81)。“基底”是什么?德里达说,subjectile是一个支撑物、一个工具或一个妖魔,它忍受着所有躺下或砸在它身上的东西,像人躺倒或把东西抛掷在纸上一样。它忍受着这些东西,但并不痛苦。它接受并容纳一切,像一个普遍的容器。也代表着场所,代表着所有人物的放置,但它不居有什么。它等待一切,关注一切,而并不动容。它既非父体亦非母体,不属阳性不属阴性。反过来说它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是抛掷和下坠的通道,也是主体本身。阿尔托写道:“迟钝的材质在我的手底下什么都没有说。它们如磨盘石一样给到我,这并不会激发绘画灵感,但我可以将基底刺、切、刮、锉、缝、拆开、撕碎、砍、编织,而不会让这个‘基底’(subjectile)经由父体或母体发出怨告。”[12](PP136-137)德里达在这里看到解构的新义,它不仅仅是主体通过“离基”(abgründ)而“建基”(gründung),通过毁灭而建造的努力,它亦是一种支撑的“基底”,是抛投和发射,也是承接和穿透,万事万物在这基片上显形成像,是承接之上的生成。
后现代主义对于主体的态度是,“它不是一个存在于浅层表现下的、由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科学来研究的深层的哲学实在。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深层结构或深度原因要被解释的表面现象。”[13](P28)德里达借阿尔托的“基底”概念重塑了这个“表面化主体”,也使舞蹈的行动得到最形象的阐释(事实上,虽然阿尔托是在谈他的素描时用到subjectile,但舞蹈的过程甚至比素描更适合展现“基底”概念的具身化)。文慧的编舞就是在舞台上打洞,舞者不仅只是编织,他们的肢体是在做阿尔托意义上的刺穿,洞穿“基底”,撕砍那个平面,从平面抛投出去……动作诞生的瞬间,是意义或者主体显现且穿透屏的瞬间。通过“基底”事物显现,而意义伴随力量在洞穿的瞬间涌出。当主体成为去中心的一个融汇平面(德勒兹把这个平面叫作“内在性平面”(the plane of immanence),是概念的呼吸运动),就像毛孔通透的皮肤,物质能量多孔隙地进行着呼吸与互换。这样的运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它并不曾完结,而这才能够抵御唱衰主体后的虚无主义。这也是坚持在公共领域表演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信念所在,在他们展现三年灾荒回忆的记录剧场《记忆在路上》(2011)表演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充满孔洞、灼伤的舞台,它散发出比意义更具体的东西。《生育报告》(1999)里有个马桶,一打开就钻出个放声大唱的女人,舞者迅疾盖上;一打开她又冒出来亮嗓,马上又摁回去……像是这孔洞里娩出的婴儿也是从这个孔洞逃逸(溺死)的生命。这个生命体的冒与摁,这种起伏间的节律,是每个人身上的潮汐起落,是我们把自己作为抛物线抛掷又坠落的舞动,观众自己投射成为一名潜在的舞者。不是身体创造了意义,而是意义正在被穿越。“意义‘在逃’,在出神。而舞蹈,就像我们习惯说的,是在出神之中‘挺住’(tenir corps),让我们被附身,但仅仅是在某个限度之内,在狂喜的边缘。”[10](P80)
四、当下时代“直言者”的力量
肢体为重的剧场艺术拥有血肉之躯的形而上学优先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是。此前我们讲到“直言”,提到构成“直言”的几个特征。当福柯阐释“直言”时,用的例证来自欧里庇得斯的剧作。这首先是因为剧作里用到“直言”(parrhēsia)这个词,另外一点在于,讲述,尤其是剧场内当众的讲述,是一种高度接近真理言说活动的形式。无论是用嘴讲述还是用肢体语言讲述,人当众告白,这种行为就在一种分析场景下被赋予某种真实性。一件事,一种欲望,一种焦虑或者一种亟须安抚的罪恶感,当告白开始时,那种身体性暴露的一刻,那种将意图之外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一刻,移情就产生了。“这是剧场成为政治隐喻的原因,这种移情性使它被当作潜在的公共领域,形塑公共意见的关键。剧场的力量或威胁,正来自于剧场能够借移情创造一群群体,以自身令人惧怕的集体煽动力点燃并唤醒群众的感情。”[14](P62)因此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著作《颠覆的时代—算法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疯狂》(The Age of Disruption—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一书里专章辨析了我们当下时代“直言者”的力量。迄今看似最依循人人发声和平等原则建构的移动互联网络带着我们飞速到达数字流量时代,但它也使我们快速见证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早古说法: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它被一种基本的蛊惑性所支配,勇气的表达总是趋于失败。正是这一点将导致“直言”本身的倒退。这也是民主的一个伦理弱点,它与民主不可能在真理在城邦中发言时由着ἦθος(ethos:通常译作伦理,包含品格、习惯、德性、性情等)发声有关。换句话说,斯蒂格勒也许正在说那句老话:“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接着强调说,“如果民主机构不能为讲真话留出空间,让直言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是因为这些机构缺乏某种可以被称为‘伦理差异’的东西。‘伦理差异’区分了有勇气说真话的人(冒着受伤和被伤害的风险),他们是敢于反对公认的话语和其他形式的僵化言论的人。”[15](PP903-904)
谁是“直言者”?怎样的情况是“直言”的行动?在今天这个媒介传播成为强势力量的时代,是尤为要考量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要始终不停地用ethos检测周遭生命在宇宙间的位置,检测的最佳场所,正是剧场。2000年看到周围越来越多外来务工者,文慧萌生与他们合作的念头,以一起跳舞的方式,将他们的身影凸显出差异来,带进公共领域。人们将生活舞蹈工作室对现状时势的敏锐观察视为政治剧场的一种表达,当代剧场创作经验也唯有向社会的那个真实社会结构展开质疑时才算是彻底。以民工为主角,本身会被当作一种政治行为。但前卫剧场“需要重新思索的,是戏剧的物质层面,而不仅是意识形态”[16](P86)。物质层面,当然指剧场内事物的打开维度和呈现方式。舞蹈比其他艺术更直接也更具当下社会性,舞动者必须直接对外敞开自己,剧场和舞蹈本身就是侧重参与的艺术。文慧有意在创作中使用社会身体(素人)而非舞者身体,作品以30位务工者的肢体表演为重点,基本以他们的劳动内容为质料来搭建结构。作品演出于即将改建的棉纺厂厂房里,开场就是一位务工者吆喝家乡的劳动号子,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种风尚瞬间改写了空间氛围。随即和声四起,呼应着,劳动者开始自人群里亮明身份,走拢在一起。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以民间小调开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工地,也可秒变《诗经》的田野。整个作品里有许多他们在日常工地里的身体语言,滚油桶、搬重物、爬脚手架……文慧给出了劳动者之所以在场的充分理由。专业舞者身体插入其间,似乎是缝合的针脚,使整个演出可看性加强了。这个演出后来遭到一些伦理上的争议,也即,当我们用到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素人身体时,怎样看待我们和他们的权力关系。文慧也接受这个作品的争议,自认说由于排练时间所限,对那30位素人身体状态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里就涉及斯蒂格勒提出的问题,伦理的差异。取消专业舞者,取消编导,他们能不能成为言说者甚至“直言者”呢?显然很难,他们无法找到一个说话的界面。反而是可以在《与民工一起跳舞》这个作品里,展现出他们肢体的能力,生命的状态,从而来言说。而文慧作为一个导演、编舞者,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人,带领大家说话的人,这亦是伦理差异赋予的“直言”权利,这份权利多少阻挡了众声喧哗带来的致命的蛊惑。能够在“基片”“屏”(subjectile)上成像的,都不会是一个只提出判断,而不同时询问判断和提供获得判断的形式的问题,当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自带“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一点在内。而在网络、平台和算法的时代,资本和流量削弱、蒸发了我们的感知,冲走了艾斯特莱雅(Astraia,古希腊女神)的天秤,无注册门槛的社交媒体和高互动高点赞模式则进一步钝化了感知力的发展,顺势推高了各种极化趋势。剧场要达到的就不仅仅是移情以致群体狂欢,而是更强劲的“出神”(transe)能力。当《与民工一起跳舞》中的赤膊汉子们呼呼喝喝推动大油桶滚过人的身体时,被碾压的不应该是舞者,反而应该是务工者。务工者碾压务工者,又或者观众参与一起来推压过去。相同的情形比如德国皮娜鲍什舞团的作品《交际舞》(老年版),邀请了一群65岁以上舞团所在地乌帕塔的非舞蹈专业民众参与演出,素人演员要以毫无训练框架的身体投身于这个舞蹈作品。作品在一个旧舞厅上演,表现战后一代的德国民众生活。其中有一处,一位老太太站立着,所有的男性演员轮番上去触摸她的身体,动作一点点放大尺度,一点点丧失斯文。四分半钟近乎猥亵的冒犯停止于另一位体面老太太的进入,人群恢复常规,近乎癫狂的人们整整衣冠,重新归队。这样的连接方式将身体还给身体,让意义痉挛。“出神”“不是反常和病态,而是来自于一种极端强烈的感受性,一种肉体和神经意义上的敏感度。”[10](P78)《与民工一起跳舞》处理上的温和,是感知力度上的温和,ethos检测仪摆荡力度不够(但阻碍摆荡弧度的因素还需要细辨,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者的问题),造成了一定意义的失焦。社会性议题介入艺术需要小心对待,彻底的反形式会消解一切感性经验,彻底的形式则走向自闭与自封。它需要我们更强悍地拿出生命经验来,紧紧拽住艺术的衣角,和技术的时代对着干[17](P118),祭上这种仪式般的笨拙身体的穿越和过渡(从在我之内到在我之上、之外)。艺术才能带着力度和准确性伴随我们一次次重新经验,在“出神”的剧场性时刻中,将每个人从目的性和功能性的身体里,把身体给赎回来,修复被算法主义玩残的姿势,找到回应经验世界多重真实的能力,这正是当代的“直言”方式。关于这一点,欧洲的当代剧场已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此地还远远不够。真实与现实、真实感与真实性、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等纠缠的境遇,是我们此地本土生活里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活舞蹈工作室也依然在路上。
惊骇的流量之巨浪冲刷过来,“直言者”强悍挺立,承受被她的勇气挑战甚至破坏了的稳定性。他们用戏剧“直言”,测试伦理的尺度,ἦθος(ethos)是什么意思?在普罗泰戈拉那里,ἦθος指的是被赋予了人为技艺的生命的位置,是凡人的地方,是体外化的,它们也需要不断地解释自身的位置,它们在宇宙中的定位。这个点位不断地变化,却从未离开过知耻(αἰδώς)和正义(δίκη)所标出的诸神与野兽之间的位置。[15](P905)在当代剧场重建由生命和死亡、交换和占领的双重强度界定和升华的社群生命体,一个人类世的逆熵联合体,这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之后,算法资本时代直言者的力量。
参考文献
[1]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III[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王音洁.从口述历史剧场到女性历史现场—文慧的纪录影像剧场[M]//复象与镜像:当代剧场与影像创作的流动图景.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雅克·德里达. 被劫持的语言[M]//张宁,译. 书写与差异.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学报简介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戏剧影视学术期刊,1956年6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戏剧学习》,为院内学报,主编欧阳予倩。1978年复刊,1981年起开始海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更名为《戏剧》,2013年起由季刊改版为双月刊。
《戏剧》被多个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确定为艺术类核心期刊:长期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成为该评价体系建立后首期唯一入选的戏剧类期刊。现已成为中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同时作为中国戏剧影视学术期刊,在海外的学术界影响力也日渐扩大。
《戏剧》旨在促进中国戏剧影视艺术专业教学、科研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注重学术研究紧密联系艺术实践,重视戏剧影视理论研究,鼓励学术争鸣,并为专业戏剧影视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的信息和资料。重视稿件的学术质量,提倡宽阔的学术视野、交叉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投稿须知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