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当代代表性诗人之一,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陈先发诗选》,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奖年度诗人大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春季大赛翻译大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

崖丽娟:陈先发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在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上见面很高兴。这届诗歌节广受瞩目的原因很多,一是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先生等多位国际重量级诗人与会。二是诗歌节的主题设定为“诗,面对人工智能”,非常具有前沿性和讨论价值。听了您主持的这场国际性研讨会,获益匪浅,能否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您在这个话题上的主要观点?另外,上海国际诗歌节给您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陈先发:我是第二次参加上海国际诗歌节,这次跟索因卡、墨西哥诗人奎亚尔等我喜欢的外国诗人见面,交流非常愉快。受赵丽宏先生委托,我主持了这场以“诗歌创作与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国际诗人研讨会,会中的诸多精辟见解让我们受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AI大模型时代,ChatGPT必将更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颠覆既有认知方式,人工智能在赋予我们时代一种全新定义的同时,也必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我对诗歌乃至所有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对诗歌在AI背景下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我不担心AI的能力繁衍到如何强大,只担忧AI产生一种东西:欲望!如果AI产生欲望,形成自我意识,也必将滋生对这个世界的征服欲。我的乐观有两个基本理由:一是诗歌最本质的东西是生命意志力,而AI没有体温,它永不可能真正感受到一具肉身的短暂、茫然或狂喜。二是所有文学创作均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化,个体是基石。而AI只有整体,没有个体。即使AI继续发展,诗歌的尊严也将延续下去。也可能我低估了AI的自我生长能力,拭目以待吧。关于上海国际诗歌节,在与多位国外诗人的交流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成功、影响力也最为显著的诗歌节之一。赵丽宏先生是诗歌节的灵魂人物,因为他的持续推动,我们可以预期,上海国际诗歌节的文学史意义仍将进一步释放。
崖丽娟:您最近完成的长诗《了忽焉》,一时间成为了激发许多诗人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首诗有个副题:题曹操宗族墓的八块砖。首先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您是如何看待历史这一主题的?或者说,诗的历史意识在您那儿又意味着什么?
陈先发:谢谢丽娟。去年秋末我去安徽亳州,第一次在博物馆目睹曹操宗族墓的这批文字砖时,先是被惊到了,继之有喜悦、意外、惶惑等等,种种情绪一齐袭来。回来后,又找了些相关的拓片、字帖来看。这些文字砖对我的吸附力太强了。这首长诗的主标题及分节标题:“了忽焉”“作苦心丸”“涧蝗所中不得自废也”“欲得”“亟持枝”“沐疾”“顷不相见”“勉力讽诵”,就取自其中八块砖上的文字。我完全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些无名窑工,面对熊熊炉火,也可能是满脸炉灰之时,手持细枝,在砖坯未干之前,把“墓砖”这般可说是庄重、凝滞,或者说有点呆板之物,变成了一个自我抒发、感时伤逝、纵议时弊、吞吐块垒的一个平台。两千多年过去,砖上文字的活力、活性仍扑面而来。墓砖,当时他们想着是会永埋地下、不见天日的东西,一下子有了绵绵不息的生机。从资料上知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亳州市文物管理机构就对十余座东汉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发现了曹操祖父曹腾墓、父亲曹嵩墓等宗族墓群,墓群占地约十多万平方米,累计清理的文字墓砖有600多块。我见到的砖块,字体大多写得随心、洒脱,内容更是百无禁忌、大见性情。这就是一己之身面对自我时的诚实书写,不求沟通,漫无目的,像某些特殊时刻“写后即焚”的诗稿一样。这些困顿、苦闷的窑工,也超越了他们的身份、阶层、处境,触碰到了人自身: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诗性的。初看墓砖时,我脑中跃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诗人大沼枕山的两句话:“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些窑工,算是最底层的魏晋人物了吧,这些断砖残瓦上,也确有一口真气充沛激荡、凝而不散。冯友兰先生曾说:“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大致如此吧。那天,我俯身在展览大厅的玻璃橱窗上看了很久,其实我真想在这些砖前,静坐冥想一日,最好是展览大厅内空空荡荡。这些文字砖,我见到的不足百块,最近还在寻些资料看,这个系列的诗,我或许还会再写一些。

写历史主题的诗,最忌讳的是,顺着史实的脉络去描摹,那一定很糟糕。我们要写出的,不是“历史的面相”,而是“历史的心象”,应该一巴掌拍碎了,成粉末了,再去塑形,再去重构,最好能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有着“共时性”的历史。在我心里,历史不过是现实的加长版,历史只是比现实多了一层时序结构而已。《了忽焉》中的窑工,可以是,或者说正是此刻的我。语言有着这样的神奇能力。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着的日常语言,也首先是历史的,哪个汉字没有数千年了?这个不难理解——历史通过语言作用于现实中的每一个人,我写诗的语言,不仅反映了思想的现实、心灵的现实,事实上也要呈现历史的“现实态”。换句话讲,历史其实是现实的一个特殊部位。雷蒙·阿隆(法国思想家)有句话讲得非常精彩:“历史是生者为了活着,不断去重建死者的生活。”当曹操宗族墓的砖块躺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我们以即时的眼光、当下的身份、现代的理念在注视着它,它就是现实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混成现实”的一部分。它不是“扮演现实”,它就像古琴瑟声、洞箫声与当下的电子音乐合成了一个曲子,古琴声是它自身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我们在内心默然阐释着这些文字砖,我们与它的对话在展开,我们无疑就是它们在“活着时”的旁观者,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这些文字砖所携带的生命信息是没有终结的,再过数千年,它依然能打动观者的心,或者说,它的生命力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之有限性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通古今之变,语言和诗就是“通”的渠道、“变”的载体。从写作的角度,从历史的废墟上来展开“物我关系”,又似乎更利于建构出诗中开阔的空间感。我觉得有必要同时强调的是,诗的力量,足以在任何事物上留下深深凿痕,我对写什么题材从来没有很强的分别心。换个说法,我对历史题材、历史元素在诗中的存在,也从来没有任何执着。我写历史,但绝不是从中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所以也不会因此而给自己硬扣上什么文化保守主义的纸帽子。诗歌中的历史、文学创造状态中的历史,不等同于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它和我们常讲的传统二字,都是一种敞开的容器,它里面所容留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写作的资源。举个最通俗的例子,筷子,它无疑是种族的和地域的,我们以使用筷子而有别于其他族群;它也无疑是历史的,我们的繁衍史有它独到的贡献;但它更是现实的,日用而不觉。对写作而言,许多东西拿起来就用,只是一种资源、工具,就像筷子。历史这个词,既含奥义,其实也非常简单而直观:昨日之我即是今日之我的历史,手再往前伸一伸,指尖就碰到魏晋的心跳了。历史是个活体。阿莱桑德雷(西班牙著名诗人)说:传统与反传统是同义词。我更愿意听到的评价是:“《了忽焉》是个新东西,它有了历史的体温,又洞穿了历史。”
崖丽娟:正如你诗中所说,是砖上的文字给了这些没有生命的黏土砖“以汗腺和喘息”。那么,您觉得文字足以揭示历史的本相吗?又该如何看待语言在一首诗中的使命?
陈先发:说来挺有意思,我们的先贤大哲们,对语言是否具备呈现真理性内容的能力,其实是不信任的。不信任的痕迹处处可见。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讲“不言之教,无方之传”,禅宗六祖慧能讲“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和“诸法美妙,非关文字”等等,充满了对语言的疑惑。在先哲们那里,老子的“道”、慧能的“本心”、王阳明的“良知”等,都是一种对语言的超越性存在,这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不可言说之物”是大致类同的。
这似乎是我们在语言中的两难之境:一方面向往不立文字的心心相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文字来作永无止尽的阐释。当然,禅宗讲不立文字,也不是绝对地不写些什么,更多的是在隐喻“指月时,眼睛不要只盯着手指”。我一度在这个问题上是悲观的,觉得文字不足以揭橥历史的本相,它所展开的,只是对历史的想象而已。不光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呈现所有的真理性内容上,文字乃至语言之力都是孱弱的。如果此处要为写作二字新下一种定义,也许只能是这样的:写作即是一个人对上述能力孱弱的“自知”与“不甘”。
从这个维度,写作的无力感,或者说写作本身具有的消极意味,来源于我们总是企图述说那不可言说之物。我们通常讲一首诗好,是感受到了“在诗之内、言之外”,有那个不可言说之物的在场,甚至是你感觉到了冰山不出海面的那个庞巨的基座部分,感受到它的压力、气场、逼迫感。这种感受的传递,对一首诗的阅读功效是关键的,但也没有办法说得过于清晰。此不可言说之物,是喧哗之所以被听见的、让喧哗现身的巨大沉默部分。我们写诗,也因为深信诗有以言知默、以言知止、以言而勘探不言之境的能力。
你提到“使命”二字,我觉得大有意味。我举个例吧。我曾被一张照片深深打动,很想为这一刹那写首诗。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太空探测器,于1990年2月14日在距地球67亿公里处,接收了人类最后一条指令,“回望”了地球一眼并拍下了如沧海一粟般、地球在深空的照片。据说在此一瞬后,旅行者1号便一去不返地没入了茫茫星际。这个场景当然是人类实践的壮歌,本质上它同时是一曲悲歌:是人以一己之渺茫之薄弱,面向宇宙之无垠时的向往、对峙和最终无望的和解。这次“回望”太动人了。因为它饱含了人之寄托,所以才谈得上使命,负得起回望,但它的命运又终是杳不可测的。这就是一个诗人在无限的语言空间中,一首诗在无尽的时间旅行中的样子吧。

崖丽娟:为了做好访谈,近期我集中将您2009年前后创作的五部长诗《白头与过往》《你们,街道》《姚鼐》《口腔医院》《写碑之心》,重新都读了一遍。虽十余年过去,仍为它们的精神气象与心灵容量所震动。有诗歌写作经验的人深知,写短诗可能更多凭灵感,而这种四五百行的长诗写作,非常消耗心力和时间,更考验耐力。我想了解的是,是什么触发您写一首长诗的决心?您觉得在长诗写作进程中,哪些东西是非常重要又难以把握的?
陈先发:写长诗往往是迫不得已。当一团面粉在你手中剧烈地发酵了,你不得不找个大点的袋子装下它。长诗正是这种“大袋子”。你很难想象一种巨物要硬塞在一个微小躯壳中,聂鲁达《马丘比丘之巅》、艾略特《荒原》中的纵横激荡之思,岂能在一首短诗中得到舒展和尽兴的表达?但我也总听到有智者在说:长诗是可疑的。
确实,长诗写作是个巨大挑战。语言推进中的考验当然很多,我觉得最难的是两样:个人语调的形成,以及,一口气如何在巨大结构中自由呼吸。语言的基调和语气的运行,是一首诗中根本的东西。这两者也算是互为表里的,语调关乎语言的呼吸、色彩、活力等等,诗之沉、之思、之宏观建构,都需在这种语调中去层层呈现,走向纵深。语调与诗之所思不匹配,就会有不伦不类的感觉。有些诗,读两行,就读不下去,为啥?语调不对——你这盘菜烧得味道不对,即便烧的是山珍海味,也没用。语言的味道是第一驱动力。只有语言的快乐,可以破除长诗中容易形成的语言的疲倦。我在动笔之前,反复琢磨的东西和最费脑力的就是这个:语调。定了语调之后,就要考虑“一口气”如何在各个部位穿行,如何在相对庞大的格局与建构整体中保持细节的生命力和柔韧性,如何让这口气在数百行诗句间自如贯通。难就难在,这口气的自由接续。没有了这口气,长诗很容易沦入字词的泥潭,必须有这口气催动语言的灵性引导着你,往结构的深处走。没有这口气,数百行长诗焉能不让人生出累赘、堆砌之感?有些长诗,思不可谓不深,力不可谓不沉,但看得出作者太想往诗中塞东西了,结果弄得面目可憎。诗的丰富性,不是靠充塞来完成的。
有两点体会:一,“营造空白”很要紧,甚至可说是让长诗活命的一招。在结构中设置大片的空白、空地,以容留阅读的自如转身,来促成写与读之间美妙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结构中的空白,往往是思想的充盈之处。在叙事、情感、语义演进的过程中,突然形成断裂,带来空白,这空白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让空白说话。空白,在恰当位置上的表现力会出人意料的强大。二,让长诗内部出现各类声音的交响。长诗是个复杂的空间,也是个自足的生命体。它的内部,必须充满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声音。佩索阿说:“我没有哲学,我有感官。”大家都明白,长诗重思。越是重思,越是要让感官的体验系统得到充足的释放。从诗中“听出什么”,是种微妙的阅读体验。最美妙的感受是:从同一首诗中每次都能听见不同的声音,这并非你的耳朵特异,当代诗释放的本即是一种变化、变量、变体。与其说你听见了诗中的一种声音,不如说你听见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你听见了什么,来源于你想听见什么。写作与阅读间,横亘着动荡不息的戏剧性连接。好诗所创造的另一种奇迹是,它让你听见的声音,根本不来源于耳膜。你的每一个毛孔、每一组细胞、每一根脑神经都有倾听的能力。你能目睹自身的“听见”。在好诗中,词之间的碰撞也仿佛是有声音的。词与词之间有一种奇妙的相互唤醒,有时与作者的写作意志并无关联。写作中所谓的神授,其实是一个词以其不为人知的方式和气息唤来了另一个词。它让你觉得你所听见的声音,出自你的生命而非眼前这首诗。
我过去的几首长诗,累积了一些想法,但其实也攒存了许多力不从心的遗憾。《白头与过往》意在从一对魔术师生平叙事中打通现实与幻相的关系;《你们,街道》展开的是对后城市化的反省以及对“破与立”的辩思;《姚鼐》是对我家乡桐城先贤致敬并进而打开一种命运图轴的诗;《口腔医院》其实是一首企图精研语言与人关系的一首诗;《写碑之心》是祭父之作,在我父亲逝世两年后才爆发而出。从语言能力而言,这些诗中精神的、情绪的、情感的、语言层面的能量,都不可能浓缩于一首短诗中。也可能一场大风雨,必须要在旷野上行进。当然,不是讲短诗中不能有宏大的内在空间,说到底是能力的局限问题。
曾有诗人跟我讨论过,长诗中如何处理繁与简的关系。这个确实是个微妙处。我的想法是,细节宜繁,针尖上的舞蹈要足够;大处宜简,否则容易沦为空响。要看具体情况,繁简并无高下之分。在《黑池坝笔记》中我曾写过一段话来讨论这个问题:“范宽之繁、八大之简,只有区别的完成,并无思想的递进。二者因为将各自的方式推入审美的危险境地,而迸发异彩。化繁为简,并非进化。对诗与艺术而言,世界是赤裸裸的,除了观看的区分、表相的深度之外,再无别的内在。遮蔽从未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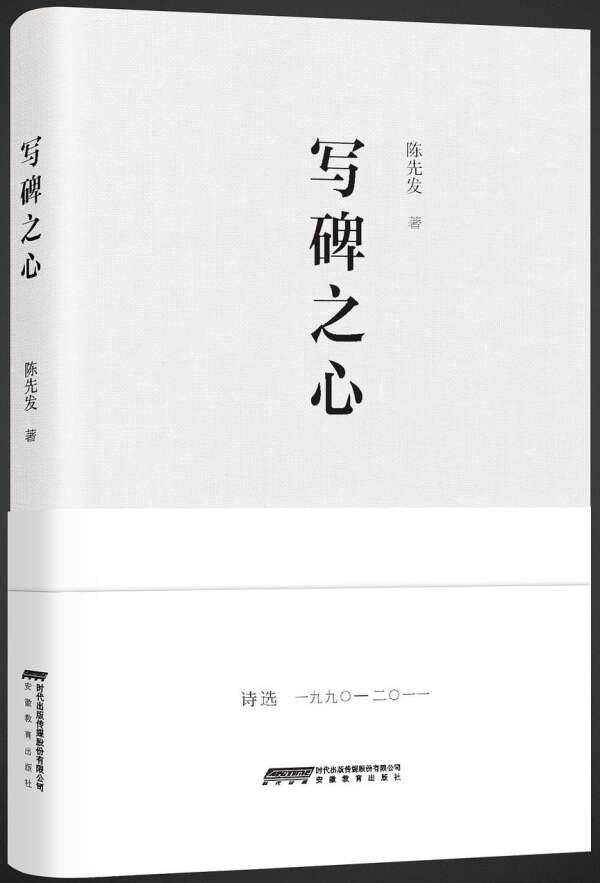
崖丽娟:我一直关注您在创建新的诗歌形式上的探索,比如读到组诗《枯七首》,每一首都以“枯”为题,仿佛一部奇异的生命合唱,令人耳目一新。您是如何想到切入这个主题或者说因何耗费大量笔墨在这个意象之上?
陈先发:枯这种镜象,似乎只有中国人深得其中三昧。枯,既不是无,也不是死,以枯而生发的艺术创造力在各个领域澎湃不绝,从庾信的《枯树赋》,到李义山的枯荷听雨,再到王维画大片的枯树寒林,元代倪瓒更是画枯成癖了,宋画中诸家画枯树是各尽其妙。诗中的表达更是丰富,不全是物之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也是一种枯境。我写枯七首,不过是我个人对枯之美学的当代演绎。
写完组诗《枯七首》后,我在《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对“枯”有着数十条解读,这里我就偷个懒了,顺手摘录几条,作为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吧:
(1)作为一种起源,也作为一种目标: 枯,对那些有着东方审美经验的人似乎更有诱导力。与其说多年来我尝试着触碰一种“枯的诗学”的可能性,不如说,作为一个诗人我命令自己在“枯”这种状态中的踱步,要更持久一些——倘若它算得上一个入口,由此将展开对“无”这种伟大精神结构的回溯。枯,作为生命形式,不是与“无”的结构耦合,而是在“无”中一次漫长的、恍然若失的觉醒。对我而言,这也足以称之为诗自身的一次觉醒。(2)枯,赋予人的“尽头感”中蕴藏着情绪变化与想象力来临的巨大爆发力。此时此地,比任何一种彼时彼地,都包含着更充沛的破障、跨界、刺穿的愿望。达摩在破壁之前的面壁,即是把自己置于某种尽头感之中:长达十年,日日临枯。枯所累积的压制有多强劲,它在穿透了旧约束之后的自由就有多强劲。(3)枯是诗之肉体性的最后一种屏障。它的外面,比它的生长所曾经历的,储存着更澎湃的可能性。对枯之美学的向往,本质上是求得再解放的无尽渴望。(4)我们对同一源泉存在着无数次的丧失:对枯的理解与解构,也不会是一次性的。(5)审美趋向的过度一致、精神构造的高度同构,是一种枯。消除了个体隐私的大数据时代之过度透明,是一种枯。到达顶点状态的繁茂与紧致,是一种枯。作伪,是一种枯。沉湎于回忆而不见“眼前物”,是一种枯。对生活中一切令人绝望的、让人觉得难以为继的事件、情感、现象或是写作这种语言行动,都可以归类到“枯”的名下进行思考,但对枯的思考,并不负责厘清表象:枯是这所有事物共有的、不可分割的核心部,也是从不迷失于表相的、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面孔的“蒙面人”。(6)汉乐府和李白均有“枯鱼过河泣”诗。八大山人画脱水之枯鱼。鱼在枯去,河在虚化。撇开本义,离根而活,枯干即是自由的达成。(7)所有必枯之物,仿佛生着同一种疾病,但它带来的治愈却千变万化。面对某种枯象,我们在内心很自然地唤起对原有思之维度、原有的方法、原本的情绪的一种抵抗,我们告诉自己:这条路走到头了,看看这死胡同、这尽头的风景吧,然后我需要一个新的起点。所有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的人,都曾“在枯中比别人多坐了会儿”。(8)当你笔墨酣畅地恣意而写时,笔管中的墨水忽然干涸了。你重蘸新墨再写时,接下来的流淌已全然不同。枯是截断众流,是断与续之间,一种蓦然的唤醒。(9)人类的知识、信条、制度或感性经验,都须经受“枯之拷问”。有多少废墟在这大地上,多少典籍在我书架上沉睡:托克维尔的脸上蒙尘多深?陀思陀耶夫斯基在我案头又荒弃多久了?在某个时刻、某种特定机缘下,我将在他们的枯中有新的惊奇与发现:仿佛不是我生出新眼,而是他们的枯中长出了新芽。
《枯七首》不是长诗,因为在这七首中,不存在内在的递进结构。从表象上看,枯,是一种生命的困境,对枯的书写是向此困境索取资源——它如此深沉、神秘而布满内在冲突。人对困境的追索与自觉,毫无疑问,带来了某种新生。

崖丽娟:我和您一样都曾经长期在媒体工作,我的体会是,做媒体能接触相对宽泛的人和事,对所见所闻所触的增益和开阔眼界确实有很大的帮助,这也引出一个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您觉得现实与诗的写作之间有一种正向推动关系吗?一个人作品的丰富性跟哪些因素有关?
陈先发:见得多,也未必就是增益。千个人、百座城,也可能重复的只是一种现实。我的想法是,诗与大家平常所讲的现实没有直接关系,它只跟一个人承担的“内在现实”有关。这是两个不同质、也不等量的概念。眼观八方、内心却一无所见的人,少吗?记得博纳富瓦在谈论策兰时,有句话说得好:“不蒙上双眼,就看不清楚。”确实,真相与真正的纤毫之末,是心灵视域内的东西。诗源于闭上眼依然历历可览的东西。当然,现实世界可以刺激与激活人的内在空间,但真正诗性往往归集在斗室之中的万水千山,芥粒之内的千峰万壑。
一个诗人的丰富性与他所感受世界的维度和方式相关。引用一下我多年前写的一段话:“在一颗敏锐的心灵之中,世界的丰富性在于,它既是我的世界,也是猫眼中的世界。既是柳枝能以其拂动而触摸的世界,也是鱼儿在永不为我们所知之处以游动而洞穿的世界。既是一个词能独立感知的世界,也是我们以挖掘这个词来试图阐释的世界。既是一座在镜中反光的世界,也是一个回声中恍惚的世界。既是一个作为破洞的世界,也是一个作为补丁的世界。这些种类的世界,既不能相互沟通,也不能彼此等量,所以,它才是源泉。”
除了认知维度,诗人之丰厚,也获益于他对语言的觉悟力。语言会慷慨馈赠他一些意外之物。诗歌语言的动力机制有神秘的一面,时而不全为作者所控。总有一些词、一些段落仿佛是墨水中自动涌出的,是超越性的力量在浑然不觉中到来。仿似我们勤苦的、意志明确的写作只是等待、预备,只是伏地埋首的迎接。而它的到来,依然是一种意外。没有了这危险的意外,写作又将寡味几许?
许多好诗是令人费解的。作品的丰富性,有时也出自读与写之间的复杂交织。好诗往往有迷人的多义性,它部分来于作者的匠心独运,部分来于读者的枉自多解。好的诗人是建构的匠师,当你踏入他的屋子,你在那些寻常砖瓦间,会发现无数折叠起来的新空间。当你第二次进入同一首诗,这空间仍是崭新的,仿佛从未有别的阅读打扰过它。
崖丽娟:您在写作中有没有出现过难以为继的停顿阶段?怎么度过这种个人危机的?
陈先发:难以为继、犹似身陷语言的泥泞之感,不仅在许多时刻有,甚至算是我的写作常态之一。一些作品,往下写不动了,就歇一歇,甚至直接撕掉,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那种一气呵成的、灵光一闪便挥笔而就的作品,当然也有,更多作品是在疙疙瘩瘩、渐行渐悟中写成的,前者只有感谢老天,再愚钝者也有暴雨直击天灵盖、灵魂出窍的那一刻,但我觉得后者才是正道、大道。难以为继,甚至忧心如焚的时刻,恰恰是珍贵的,它构成了写作中困境与超拔的原力,是锤炼人的好道场。慧能讲得好呀:“烦恼即菩提。”
艺术说到底,是个体生命力的激发,是一个易朽与短暂的生命体,在孤独时告诉自己如何去追逐那不朽的愿望。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只有两样:我们的卑微与我们的滚烫。一己直如蝼蚁,人面对无垠时之弱小,人面对速朽时有真情,是这两样,令我们拿起笔来。这杆笔,也唯有经过千锤百炼甚至是艰苦卓绝的一个过程,才能真正形成价值。
崖丽娟:目前正在进行的作品有些什么特点?您的自我期许,是在哪些地方获得突破?
陈先发:手头最重要的活儿,是系列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的第三卷,争取明年初出版。前两卷是2014年和2021年出的,这中间的间隔拉得太长,我期待以后这个系列完成和出版的密度加大些,节奏加快点,一年出一新卷最好。这是一套百无禁忌的游思录,写作的主体内容其实早已完成,现在是整理至第三本。整理,我并不视作是简单地归纳,而是再造,重新为这些言说的碎片集确立一种内在的秩序。更重要的是,第三本如何突破前两卷已经形成的某种惯性,是我正埋头处理的一个要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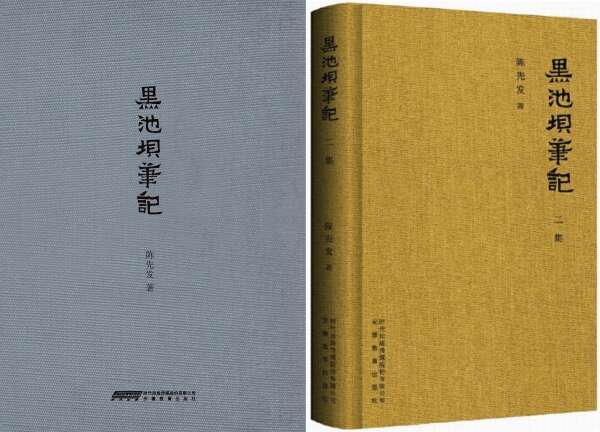
另有些列入写作计划的大体量作品,比如,一部有关量子纠缠的长诗,是一个新的维度交织着新的难度,能不能最终写成,还很难说。还想着手写一本长篇小说,我在小说上的经验积累较少,二十年前尝试着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拉魂腔》,从淮河灾难史中去写宗法制度在中国底层的解构,东方式乡村图景的崩塌,我对这个向度的思考一直有兴趣,也攒了些想法,有冲动再去触碰一下。写作是个人意志力的左冲右突,什么结果,难以预知。加上工作强度大,对个人时间和精力占用多,不敢说期待什么突破,做做再说吧。
崖丽娟:我注意到,今年8月份,几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广州主持召开“词的重力场——陈先发赵野作品研讨会”,能否谈谈现场有关情况?研讨会主题很有意思“词的重力场”,该如何理解?
陈先发:在这里,再一次对诗人陈陟云表达谢意,他费了很大心力汇聚多方资源,为诗人们召开专题研讨,这个系列若持续下去,当是诗史上出彩一笔。本次研讨,国内诗学理论界最活跃的一批名家都到场了,我理论根基薄弱,听下来自觉获益良多。这个研讨,我是空着双手去的,原想做个彻底的倾听者,因为要互动,所以也谈了点想法。
研讨会主题的确有意思:“词的重力场”。从文学角度观察,信息时代呈现的是“重力场”不断消解的失重状态。过去心怀壮阔的远行,现在高铁瞬间就抵达了;过去充满意味的登临,辛苦而得的一览众山小,如今缆车顷刻就瓦解了它。碎片式、即兴式、戏谑式文化景象,让“重”无所寄托,精神创造领域因之产生了巨变。恰是这种失重,令这个研讨有了远超出两个研讨对象本身的意义。
我想写作者的一个基本愿望,是唤醒一个更为内在的自我。这里的唤醒,是指发现,是抵达一种语言的“场”,或说是“态”。它大致的特点有三:一是,更为凝神、凝视、专注的自我。可能再难找到比写作更能将一个人全部身心凝聚于一点的劳作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受各种困扰、质疑、失败,常常处在生命力的涣散之中,目光难以因凝于一物而到达生命意志的深处。而写作,逆转了这种状态,我们因凝神而捕获了力量感,因专注而趋于某种超越。这个过程也是开放的、没有尽头的。谚语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诗歌的维度看,它又是“罗马是永不可能建成的”和“罗马正是一瞬建成的”的叠加状态。这个朝向单一、纯粹的途径是快乐的,所以对写作者充满了强大的引力。我的体会是,成诗的愉悦,再无一字可动的愉悦,胜过任何其他方式的愉悦。这是自我完善的道路。二是,如果写作是有效的,它一定处身于一种多维的对话关系中。与时代的对话:这个不可避免,只能层层卷入,每个人都是具体时空中的生命体,经历着时代赋予的、鸡毛蒜皮般具体问题的种种拷问。不管你写下什么,只要你对自身是忠诚的,那么你写下的每一句,都是对话的继续、答案的呈现。与自我的对话:人自身的缺陷带来了内心生活的分裂、裂变,自诘同样不可避免,写作可以视作自诘的种种变体。人被自身的目的所蛊惑,也同样对这种蛊惑抱有敌意,哪一个我,不是矛盾着的“众我”的集合体呢?与语言的对话:写作是语言的运动,对过往语言经验积累的摹写、审视、审判,对个体语言风格的向往,是写作的原始冲动之一,要时时将语言实践导向深入,那种一眼即辨的个体语言形象是如何建立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复杂性是如何输导至语言当中的?这都仰赖于写作者与语言互信、互搏的对话关系趋于深化。当然还有与自然的对话关系,在我们的文学脉络中,自然一度立身于神位之上,今天这个位置的空无,又能予今日之写作什么样的启示?总之,一旦动笔,我们就被迫在这多重的对话关系中,时而紧张、时而舒缓地进行各种再构与重建,语言的智慧与文学的进程也借此展开。三是,我们的诗歌仍需从对历史的“吮吸”中审看自身。“来处”本是一个可疑的对象物,文学史自体的变幻中也留有我们对“去路”的建构。“重力场”三个字,它当然不是指赵野和我已经完成的某种诗学特质。诗趋向精神领域的重力,早已构成汉诗的传统,从这个指向上去阐释杜甫,我们已谈论得够多了,这个重力不是指某种分量重量,“轻”的风格,也可以达到审美效应上的重力,我倒是倾向于认为,人对内在自我的发现永不止步,才真正匹配得上这重力二字。时空的位移,不断造就更新的、更深存在的自我,我们面对它永远存在着新的“匮乏”,这个敞开的精神容器永不可被填满,我们对此种“匮乏”的渴求甚于被喂饱的渴求,这是“词的重力场”的真正要义。今日之现实,不再是历史的某种线性延续,科学的突进让人的视域由原子、夸克、量子的递入而趋向令人窒息的精微,生活的现实,已陷于虚拟空间强行插入的“混合现实”“超现实”的多重围困,我们一度弃置的文化态度中,我们对文化态度选取的两难之境中,是否真的埋伏着可能新生的命题呢?这些是研讨会上即席随兴的想法,肯定不够严谨,留待以后的写作实践去延续吧。
(崖丽娟,壮族,出生广西,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评论。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其中《会思考的鱼》荣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编著有10余部文史书籍,在各大报刊发表新闻报道、传媒研究、历史研究、文艺评论、作家访谈等各类文章1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