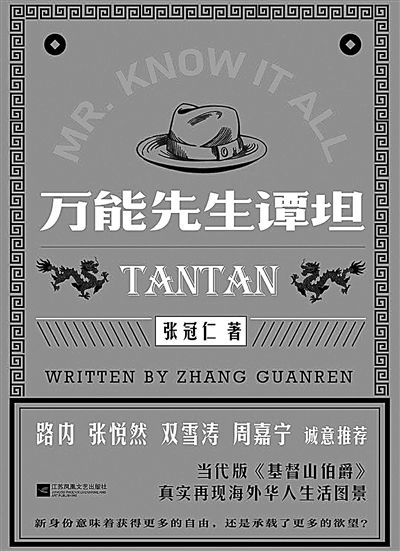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之中,所有人又都活在自己的希望之中。”在长篇小说《万能先生谭坦》的结尾处,作者张冠仁终于忍不住抒了一小段情,算是为这本始终克制陈述的小说,留下点睛一笔。
《万能先生谭坦》算是写实主义小说?还是“新移民文学”?要么干脆只是通俗小说……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将读者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一群陌生的人身上,发现我们自己——在全球化时代中,人人已被置身于“边缘情境”:我们弑父,我们遗忘,我们扮演,我们迷茫……所谓“万能先生”,不过是漫长却终会破灭的白日梦。
仔细看小说主角谭坦,不过是单薄的纸片人:只有履历,没有自我;只有异能,没有个性。他如此完美地契合于“必然”,却又被“意外”粉碎。隐喻着成功弑父之后,他将成为下一个被弑者。
这个“从弑父到被弑”的怪圈绝不只发生在当下,也非全球化特产,而是一个古老民族百余年挣扎的文学概括——已经破茧,却难化蝶。
《万能先生谭坦》揭开了太多人心中的暗伤。
爽感来自“叙事射线”
说《万能先生谭坦》是写实主义,体现在两点:
首先,以人物为中心,专注于情节,而非细节。
其次,作者谨慎地躲在叙述背后,努力呈现福楼拜推崇的“圆滑如球”的世界。
小说第一章如教科书般的赏心悦目:从边缘人物叶瞳瞳引起故事,引出谭坦的七号助理乔治孙;再因乔治孙同时接到客户Sally代考的请求,引出他的昔日情人、学霸雪梨黄;而雪梨黄正因闺蜜周怡赚钱能力而震撼,准备改行;其实,周怡当年是通过蛇头来到英国,刷了几年盘子、不惜手段上位后,才进入生意的蓝海……
从一个人物引起另一个人物,过电般串联起来。谭坦未出场,作者以《红楼梦》式的“三染法”写来,便是“无声胜有声”。
在小说前半部,隐含着一个叙事射线:以不可回溯的手法,渐次呈现整个叙述侧面——旅英华人社会。其中人物命运相似,面相皆不同。
“叙事射线”的优点在于:
其一,契合人类经验的形成过程,我们总是先从一点,渐识一线,再知一面;
其二,概括性更强,用如此少的篇幅(247页,15万字),写入如此多的人物,每个人有不同的前史和偏执,且能保证故事量,如用传统写法,四五十万字未必能装下。
如果说《万能先生谭坦》中有内在的爽感,那就是“叙事射线”带来的红利。
悬疑来自人,而不来自事
《万能先生谭坦》的故事不复杂。
上世纪80年代初,谭坦的父亲偷偷搭上国际货轮,去英国“捞世界”,与年龄相仿的杨仲英同行。杨是遗腹子,父亲早年去英国打拼,成了华人黑帮老大,因受伤丧失生育能力,托人到国内找独子杨仲英,去英国继承家业。偷渡船上,杨仲英失足落水而死,谭坦的父亲遂假冒杨仲英,一夜暴富。因转做正经生意,特别是在中医推广上做出贡献,谭坦的父亲成为侨领,代价是终生扮演杨仲英。
谭坦的母亲得知真相后,忍耐、等待、期望瞬间清零,因纵火自杀成了植物人,当时谭坦才10岁,4岁的妹妹精神失常,智商永远停在4岁,这成为谭坦报复父亲的借口。
在这个变形的《基督山伯爵》的故事中,怎样才能嫁接上新的悬念呢?《万能先生谭坦》的高明在于:它的悬念不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人物。
在小说中,“杨仲英”(就是谭坦的父亲)、乔治孙、周怡、钱博思等都是多面人,谭坦也在道德上反复摇摆:
一方面,远在英国,谭坦坚持每周和植物人母亲、失智妹妹通话各一小时,他和妓女“小东北”彼此怜悯,透露出人性光芒。
另一方面,谭坦又冷酷、险恶。对不惜代价上位的周怡,谭坦抓住她找“小鲜肉”(泡新留学生)之短,最大化利用了她;对生活艰难的医生李茜,则设局骗走1.8万英镑,彻底毁灭了她的希望。
谭坦亦正亦邪,小说写到一半,他的动机已明确,但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是什么在阻挡他、他会用什么狠招、他下得去手吗……成了新的悬疑。
结果相当存在主义:因“杨仲英”手下小沈与“小东北”一次皮肉生意,让谭坦发出“大招”。可这和“杨仲英”有什么关系?且小沈也没超常规。正是毫无关联的原因,毁灭了“杨仲英”。
当弑父成为传统
“杨仲英”被毁,有偶然,也有必然,根源来自旅英华人群体的内部撕裂。在《万能先生谭坦》中,精描出“冰火二重天”。
一边是老胡、医生李茜们的世界。因身份不合法、收入低、不肯亏心,又要承担起远在故乡的家庭责任,他们接受了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命运。在传统社会中,还有舆论、人情世故等约束,可在移民群体中,这些“弱者的武器”已无效力。除了老胡、李茜等老一代,叶瞳瞳等新一代也被编入了血汗链条,为了生存,她忍受着每小时3英镑的超低薪,为此耽误学业,差点儿被驱逐,只好向谭坦求助。
另一方面,是“杨仲英”们的世界。他们习惯了掠夺式经营,所谓专业度,无非是彼此倾轧、压榨弱者,以鸡鸣狗盗为荣。他们表面光鲜,却缺乏资源,同样遭遇歧视;虽手握重金,可不压榨员工,很快就会破产。面子与里子的分裂,内化成人格分割。“杨仲英”满口中医利益、民族光荣等,也不全是谎言——在旅英中医企业残酷竞争下,他希望恢复传统的约束力,却又想受益最多,这恰好是重建中的最大困难。
事实上,恰恰是“杨仲英”们率先完成了精神上的弑父——通过反叛原有社会秩序,他们逃离故土,在异域实现独立自主。可离家容易回家难,不受约束的精神与肉身的沉重相互拖累。毕竟,活着从来不是件容易事,何况欲望会不断增长,它如枷锁,羁绊着心灵自由。
当“杨仲英”们历经折磨,勉强在灵魂与肉体间达成和解后,后代却不愿接受他们的方案,他们又成了新的弑父者——结果,一代代的努力未能有效地积累成传统,反而是弑父,变成了传统。
恩怨让他们忘了,整体正在崩塌
在几乎所有后发的传统国家中,都面临着“精神上弑父”变成传统的困境。
从莫言的《红高粱》,到《红发女人》,再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关“精神上弑父”的主题此起彼伏。《万能先生谭坦》则直指其根源——身份危机。
在常态社会中,身份一般处于隐含状态下,只有个体与社会出现危机,身份才会凸显出来。换言之,只有开始追问“我是谁”“我应当如何”时,身份才会变成一个问题。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
对于旅英人群来说,“明天会住在哪里”“会不会被饿死”“如何摆脱贫困状态”是经常要面对的议题,正如书中的叶瞳瞳,突然发现信箱中会出现那么多信,她离被驱逐,只剩最后72小时。她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当然不是,而是她一直想回避、遗忘,这让她“视而不见”,于是,麻烦不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
“刻意忽略”与“局面突然恶化”构成持续的威逼机制。
正如书中的老胡只剩同情,无力再爱,正如李茜想悬壶济世,却被一步步逼成杀人犯。不安全感来自身份的不确定感——今天是人人羡慕的“海漂”,明天可能就是灰溜溜的“海龟”;别人以为你在发大财,其实只是“看不见的人”。
身份压榨下,生命只能变得粗糙、冷漠、荒诞。于是,谭坦必须用弑父来悬挂自己——惩罚那些将自己逼入身份危机的人,就是生活的目的。在谭坦身上,只有执着——定时起床,遇事先订计划,和助理只有最低限度的沟通……通过隐藏自己、惩罚自己,来把恨误读成爱。而在人性恶的循环中,中医在英国由盛转衰,大厦将倾,却人人自保,终于沦为一片废墟。
拓展了移民文学新路
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移民文学的价值何在?
大多数移民文学用母语写成,对所在国文学影响不大,可对故乡来说,这些写作又包含了太多陌生经验,很难形成共鸣。于是,许多移民文学成了个人奋斗的自传,成了以文学为掩护的自我炫耀。
《万能先生谭坦》则拓展出一条新路:以旅英人群的变迁,隐喻故乡社会的成长。
中国近代化是在“船坚炮利”的压力下舶入的,并非本土传统的自然生长,由此引发“古今之变”,即站在本土文明的逻辑上,很难理解“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清末中国知识群体深感困惑,为什么靠掠夺、杀戮、欺凌、贩毒,而非公理正义,也能左右国际秩序,难道“千秋胜负在于理”已经失效?当他们接触到进化论后,很快便全盘接受,他们终于找到了合理解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他们坚信,这就是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
其实,接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恰恰是身份危机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几代人的心态失衡、过度竞争,精致功利主义日渐茁壮。人人争取个体利益最大化,却成整体的渊薮,不知不觉间,落入“一代人推翻前一代”的弑父循环中。
《万能先生谭坦》的价值,正在于用一个相对陌生的模型,呈现出弑父循环的怪圈——每代人的努力,不过是给后人提供毁灭自己的理由。那么,《万能先生谭坦》真的只是一个悬疑故事?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孤岛”,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与希望中,当彼此伸展、组合成一个闭环时,如何打破它,就成为值得深思的议题。用世界眼看中国、以普遍困境反思现实,即《万能先生谭坦》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