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史景迁在其著作《王氏之死》中曾对这位湮没于历史中的女性有这样一段饱含情感的比喻:“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却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像“王氏”这个语焉不详的名字所指称的,女性总是深埋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后世的人需要破除重重雾霭才得窥见一鳞半爪。中国古代历史中,讲故事的常常是男性,他们的故事里,女性总是作为一种附庸、一个陪衬、一个佐证。
妇女节,着眼于历史中的女性形象,从下面这些史学研究中,我们会读到,当讲述者尝试以一种理解之同情仔细地于历史迷雾中爬梳,当故事主体被置换为总是沉默着的女性,当丢下那种长期阴云一样罩在女性头上的伦理教化、以新的方法与新的材料富有创见地讲述,故事会变得多么不同。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是一篇体量不大的论文,但它从一处小小的坟茔讲起,完整讨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即推行一种看似更普适、更遵从“节孝双全”的伦理文化时,女性形象和女性故事是怎样被抹除和篡改的。
 姑嫂坟
姑嫂坟
文章中所主要讨论的“姑嫂坟”是广州市北郊白云山麓的一处珠江三角洲的大族——番禺沙湾何氏的祖坟。“姑嫂坟”的墓主人是沙湾何族四世祖何人鉴的妻子与妹妹,而有趣的是,在同一墓地内,还有何氏三世祖何琛、四世祖叔何人铎(一说是何人鉴的胞兄,一说是何人鉴的堂兄)和九世祖的墓。和中原文明很不同的,当地绵延到现代的何氏家族延续着家族惯例,以“姑嫂坟”、而不是男性祖先的墓葬作为祖坟。
作者刘志伟剖析了当地的历史背景——岭南地区在秦汉以后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直到明代以前,都与中原文明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女性,无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扮演者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
故事主体何氏宗族声称其祖先于宋朝迁居广州,而彼时,当地女性地位很高,宋代文献记载“番禺……妇代其夫诉讼,足蹑公庭,如在其室家,诡词巧辩,喧啧诞谩”“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由此可见,女性非常强势,绝非仅仅局限于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且当地女性嫁妆丰厚、且有相当比例的自梳女。
作者考证,“沙湾何氏的始迁祖何人鉴据说是借助宋代名宦李昴英的关系定居沙湾的,数自年来,沙湾何姓与李姓都维持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在民间流传的传说中,有何人鉴娶李昴英的婢女为妾,其子娶李昴英侄女为妻的情节,使人怀疑其中含有何姓因入赘李姓而定居沙湾的隐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少宗族的定居传说,都与女性祖先有关,把女性祖先的墓地作为祭祖对象、沙湾何氏也不是惟一的特例。”
至此,为何崇尚“姑嫂墓”其实已真相大白,但值得玩味的是,何氏家族与当地人怎样讲述“姑嫂”的故事,当地流传的版本其实相对简单,不过是姑嫂关系甚笃,而当地自梳女风气盛行,因而姑在嫂子死去以后未嫁,最终老死,并与姑合葬。
这个没有男性主体的版本显然不能令士大夫们满意,乾隆年间,清朝的一位官员就应当地何氏的一名士绅要求,写了《姑嫂坟碑记》,为“四世祖”补了相当多迂腐俗套的情节:
生起而对曰:……时值乱离,四世府判公奔走王事,常外出,姑嫂晨昏侍,衣不解带。姑以本生宜报,嫂也贤劳……姑嫂二人相依为命,公亦怡然忘老,越数年,公殁,嫂哀毁未几得病殒身,时姑无恙,一恸而昏迷,与嫂同日弃人间,府判公义而怜之,俾合葬于先人墓侧,以慰其本志也。邑乘只载其姑嫂相得之情,不无缺略云。余曰:……
姑嫂坟的传说经过重新解释后,一个普通的民间传说,成了士大夫推行道德教化的寓言。本来只是关于姑嫂之间友爱相洽的故事,在“碑记”的版本中,注入了姑嫂孝敬父兄的内容,这一以男性为中心的角色定义,使故事中的女性中心的主题转换成了一个男性中心的主题;故事主角姑和嫂身上那种在原有的土著文化传统体系中的女性形象,被按照士大夫的伦理价值规范重新塑造之后,成了正统的士大夫文化体系中的女性形象。
由于《姑嫂坟碑记》是最符合士大夫道德礼法的标准版本,这个版本显然被何氏家族的男性广泛接受,乃至在1994年,值姑嫂坟迁移重修的机会,沙湾何姓族人以“番禺市沙湾镇重修姑嫂坟筹备小组”的名义,专函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要求“在重修姑嫂坟时复置其父翁何琛之墓”,该函论证修复何琛墓的理由是:
今我组同仁在快将重修“姑嫂坟”之际,细思白云山三台岭的“姑嫂坟”一带,乃何留耕堂的先祖墓群,当时始葬者就是何琛祖,即姑嫂之父翁也。其墓在姑嫂坟之右肩上。该墓在永乐和天顺年间先后被人侵葬,几至湮没。但每当清明祭扫时仍按慕穴方位,焚香点烛,一样祭扫,今次“姑嫂坟”幸得获准确定为广州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快将重修。
理应恢复三世祖何琛公之墓。虽云能确定为重点文物者,“姑嫂坟”耳,而我组认为:如无何琛祖之病与殁的发生,就显不出嫂对翁之晨昏侍奉,夜不解衣的贤劳阃德,此其一也。亦体现不出姑对其父的节孝堪嘉、姑对其嫂之情爱深厚,此其二也。……
至此,姑嫂传说有了一个更“合于体统”、更能教化女性三从四德的、符合士大夫礼教文化的面貌。
《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
这本书中,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伟然在这本书中尝试将历史地理研究与女性研究相结合,提出“亲情伦理规则在宗族环境和无宗族环境下迥然不同”的判断与“亲情的地域类型”学术概念,这是女性研究中一种值得被注意的研究角度。

作者希望读者能够以一种流动的眼光来看亲情关系,并对一时一地的风习小心做出判断。
书名中所点出的“讨鼓旗”是湘东南安仁、茶陵、炎陵一带存在的习俗,即每当妇人去世的时候,以死者兄弟或内侄为代表的娘家人有权在丧礼上得到一笔财礼。这笔财礼牵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主要就是娘家人吊孝之行的花费,但有时也会弄得非常复杂,甚至会将死者的嫁妆给要回去。
而这则习俗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引起不同的回响,作者认为,要理解某一风习,就要分析某一风习形成的历史人类学逻辑,张伟然谈道,某一地的文化生态会严重制约亲情伦理关系,“我个人理解,可以把湘东南一带传统社会的亲情伦理与黄河下游一带作为两种类型来对待。前者是以宗族作为社会结构骨架的,而后者没有。在宗族环境中,通过本书上篇可以看到,出嫁女的个人权益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需要娘家人为其维护,因此,出嫁女一般不可能把与娘家的关系搞得很僵。相反,总会尽可能地对娘家人予以尊崇。道理很简单,娘家人有面子,出嫁女才有面子。娘家人好,出嫁女才有依靠。一般情况下,出嫁女总会维护娘家人——包括嫂嫂——的利益。”
而在缺乏宗族支撑的黄河下游地区,亲情的构建似乎处在一种非常任性的状态,血缘的意义似乎大于一切,缺乏目光更长远的考虑。作者搜罗了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各种版本的民歌,其内容大同小异,我们可以从如下的版本中基本了解其对于女性长辈形象的塑造:“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只怕爹爹,娶后娘呀。娶了后娘,三年半呀;生个弟弟,比我强呀。弟弟吃面,我喝汤呀;端起碗来,泪汪汪呀。”这个故事在流传中成为了“继母必然会虐待丈夫前妻所生子女”这一主张的一条有力证据,几乎每一位继母都不免陷入这个困境,而这个困境也并不应该只归咎于继母之偏心和狭隘,而关乎当地整体的亲情伦理规则。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去年年底史景迁的去世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回顾史景迁的历史写作,《王氏之死》是很特别的一本,这部书中,他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底层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其中殊为可贵的是他引入的蒲松龄的视角,某种意义上以“文史互证”弥合了史料中衍漏的真实,并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史景迁在书中例举了许多蒲松龄写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和观点来谈彼时的女性处境:“我们可以就蒲松龄对女性价码的比较评估(虽然这种评估带有相当的嘲讽)编出一个价目表:和最高级的妓女过一晚可能要花上男人十五两银子,但要永远拥有这么一位美女,却得花上一千两;二百两买一个年轻的歌女,一百两买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妾;但只要花十两,就可以买到一位丑陋、坏脾气的地方士绅的婢女做妻子;花三两,鳏寡的农民就可以买到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两给书记起草婚约,一些铜钱给媒婆,还有一两多一点给新娘的家人)。”
王氏正式出场之前,史景迁花了相当多笔触去描写彼时的时代背景:1668年的一场严重的地震,郯城县6万人中有9000人罹难。而在此前,饥馑、盗匪、疾病、蝗虫和屠城的清军已屡次重创这个山东小城,这里已是肉眼可见的民不聊生,而女性的境况更为糟糕,如果某一位女性足够幸运,从屠城、饥馑中逃生,她仍旧要面对来自伦理道德的最后一重审判:《郯城县志》中关于女性的传记共有56篇,其中关于已婚妇女的记录有53篇之多,其中有多个为夫自杀的烈女的记载,“节烈”的编目中,鼓励那些丈夫死后慷慨赴死的烈妇行为,并详细记载这些烈妇如何惨烈地悬梁自尽、以头抢石,以这种肉眼可见的悲壮来竖立可资效仿的典型。
而王氏则是这种礼教观念驯化失败、作为一个反面案例被讲述的故事。王氏1671年前后与任某成婚,因无法忍受贫穷与一男子私奔,被抛弃后被三官庙道士收留。没多久,任某和邻居高某都发现了王氏,任某认为是高某将王氏藏在庙里,双方起了冲突。后任某在一个雪夜中掐死了熟睡中的王氏,并弃其尸于高家,诬赖高某与王氏通奸并杀死了王氏。
王氏的故事即便在现在讲述,或许也会被强调其中的训诫意味,但史景迁以同情之理解讲述王氏,他认为:“王氏引导我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引导我第一次进人一个在所有看得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分配上都失利的边缘县分。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许多女人像她一样,就像许多县跟郯城一样,受苦受难,缴租纳税,然而回报却很少。”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
同样以女性墓葬的角度切入,《世变下的五代女性》研究视角与研究材料进行了创新,立足32帧女性墓志碑文,她们的身份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女子、平民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其身份多元,呈现了一幅五代女性群像,借此得以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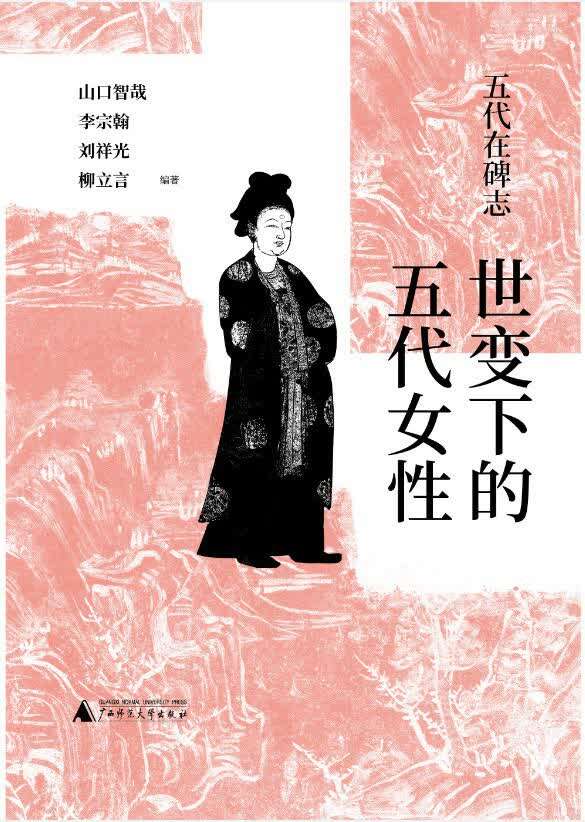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更加学术,仔细梳理和讲解了每一方墓志,用传统的史学方法把墓志的资料分门别类,数算篇幅,不但看女墓主本人的所作所为和特殊面貌,更看其他人物的作为,例如找出娘家的父母、兄弟、姊妹,夫家的婆婆、丈夫、儿子、女儿、妾妇等人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彼此对照,才能发现女墓主的“相对”重要性,是主角还是配角。进一步追问,女墓主凭什么条件成为女主角,其他人物又凭什么条件成为男主角、第二主角或最佳配角?这些条件是各自为政,还是不无共通之处?那些共通之处,是符合还是违反传统礼法如男女、父子、夫妻、兄弟、嫡庶、正室侧室的先后次序?违反的情况是特例还是普遍?如是普遍,是否反映不少求志者、撰志者以至当时人的价值观念,是把各人对家庭的贡献置于首位,超越性别、尊卑、长幼、贵贱的考虑?等等。
作者认为,对于墓志的研究和其他研究相仿,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者们都是先入为主,把传统礼法或明清时代的价值观,往前代女性的墓志一套,从男尊女卑和女无外事等角度切入,认为女性不能成为主角,本身“有事亦不可记”。她的优、劣取决于她对相关男性所能发挥的功用;即使是女墓主,都缺乏具体的身影,仅能以一种面目示人。研究者造茧自缚之后,遇到矛盾之处,如女墓主清楚是主角,明显有外事,便认为是撰志者的策略性调整或救济性笔法。
而仅在这32方墓志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五代女性扮演的世变中的贤妻良母,除了具备传统的美德,还要帮助夫家的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
也是在墓志这种体裁中,读者可以看到相对更生动的女性形象和更具颠覆性的故事,《 五鬼搬运夫死从妻 (郎氏、刘氏)》中,即塑造了一位主要凭丈夫成为官夫人的女性,她的墓志没有记载亡夫家世、亡夫名讳和半点具体业绩,她的角色主要是在丈夫死后主家二十多年,对外是“追游豪贵,轸悯孤贫”,当然还有投资买卖签契订约,对内是“不失旧规,一如常则”,负起维持家门的重任,那是一个四代同堂并不好管的大家庭。为了葬在宜子宜孙的福地,寡妻死后不从夫,反要亡夫就己,从原来的墓葬搬来一处重新挑选的风水宝地合葬。
藉这些墓志观察五代至北宋社会家庭史的连续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变读者对女性“男尊女卑”“无所作为”的固有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