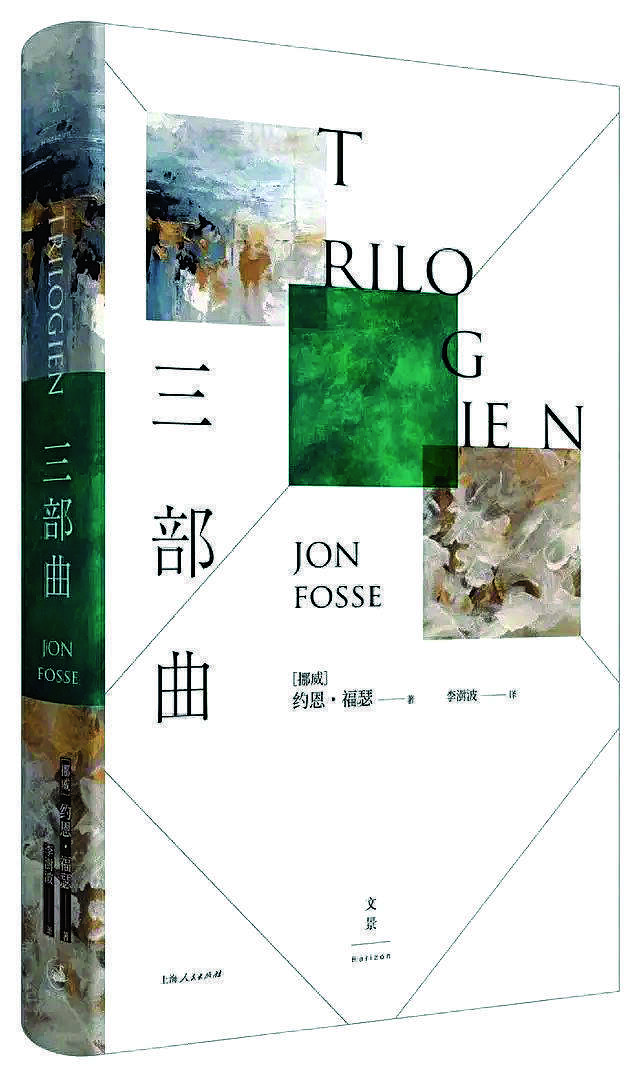

“是谁曾经说过的?——‘所有的旅程,都是归程’”,这是我第二篇有关福瑟文章的结束语。自2003年冬拿到福瑟的第一个剧本《有人将至》开始,自2004年完成翻译开始,自2005年在《戏剧艺术》发表开始,自2009年暮春在潮湿的挪威西海岸城市卑尔根与作家在雨中那些漫长的散步与倾谈开始,译介福瑟的旅程,我已走了近20年。而这趟奇异的文学与生命之旅,未来仍将继续。
当我们谈论福瑟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曲折的前行中,除了福瑟戏剧文本的译介与出版,和对其整个文学生涯的不懈研究,从戏剧院校到专业院团,我也始终致力于将福瑟的舞台文本在中文世界中搬演。2023年初秋,当作家获奖的消息传来,一片“喧哗与骚动”之中,被论及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福瑟剧作的舞台呈现。那么,当我们在谈论舞台上的福瑟文本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些什么呢?或许正如这位“以另辟蹊径的戏剧和散文体作品,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的一切以声音”(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作家本人所说的那样:在这众说纷纭的时刻,我们更应回归文学本身。因为,这首先是文学的胜利。所以,当灯光熄灭,“天使穿越舞台”(福瑟早期文章标题),嘘……让我们一起来静心聆听他笔下的文学乐章。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的一切以声音”的作家,他笔下那诗意澎湃,又无比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庸常人生的文学作品本身,也是“难以言说”的,尤其是他的戏剧。2010年的那个秋天,作家本人曾亲临上海,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剧场的最后一排,观看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有人将至》的中文版演出。
曾有播客节目的听众问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版本是中文的吗?福瑟先生看字幕吗”?巴别塔巍巍而立,但一个因素在跨语言交流中始终是重要的:那就是几乎所有语言各自的美,都与音韵和节奏有关。福瑟戏剧中的语言,尤为如此。他曾说过,写作毋宁是一种倾听。所以,那晚他静静坐在剧场最高角落的时候,仅凭这一点,他便可辨别。更何况,作为写出这些戏剧语言的作者本人,对每一个文字节点的情绪展现,都是了然于心的。
但的确,在福瑟作品中,在我称之为Fosse-esque式的、不可复制的“福瑟式”美学宇宙中,在诸如极简主义,重复与静场,节奏感与音乐感等鲜明的语言特点之外,福瑟戏剧的舞台呈现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来自于它的主题——自始至终,作家的目光都凝注在那些既是日常,也是人类亘古的普遍困境之上:交流的无效与挫败,对爱与关系的渴望,由此而生的西西弗斯式的追寻,以及,所有爱与关系的死亡和丧失。作者笔下用来呈现这一切的语言,或只是“寥寥数语”,但对在时间荒原上踽踽独行又偶尔相逢的我们,透过福瑟的舞台文本触碰到的,却是那些蓦然出现却直击人心的最真实最隐秘的生命际遇和体验。或许也是最黑暗的。
瑞典戏剧评论家莱弗·策恩曾说过:“福瑟是在为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而写作。唯有在演绎者和观众共同的梦境中,这个时代才能到来。”从这意义上说,福瑟始终是一个超前的作家。只不过,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我们仿佛更能贴近他作品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离触摸他作品的脉搏更近了一点……
如果我们愿意回想《有人将至》的开场与终局,在这个全世界被搬演最多的福瑟剧作中看到的很可能是生命里关系模式的不断循环与往复:对爱与交流的渴望,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挫败,生命中所有最珍贵的一切都随着时光缓缓褪色与消逝……然后,从头再来。在我们自身的生命历程里,在舞台上他者故事里,“将至”即是“已至”,开场即为终局。
变与不变之中,日常的幽微得以描摹
在创作主题上,福瑟写的从来都是人生最本质的存在和状态。这些经历或感悟,虽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的(哪怕只是一刹那),却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去面对,更遑论自我审视与剖析。因为,对生命最本真状态的凝视,需要太多的勇气和能量——对读者和观众来说是这样,对那些在舞台上创作和搬演福瑟戏剧的艺术家们而言,更是这样。没有读者/观众的福瑟文本/戏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当观演双方都投入彼此交融的时刻,两维的文字与三维的舞台呈现的意义,才能得以真正达成。
另一方面,福瑟笔下那贝克特式的精准舞台提示,那意味深长却又未曾抑或无法宣之于口的,如潮水般暗流涌动的潜台词和言外之意,既像中国画中的留白,也像音乐:曲水流觞中有急管繁弦,“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福瑟剧中的人物对白常常寥寥数语,却仿若汹涌而至的峡湾浪潮,巨大的情感张力,瞬间就能将读者与观众置身情境之中,彻底淹没……
在舞台上沉默,或许比滔滔不绝地说台词要难上一万倍。福瑟剧作中无处不在的停顿/静场,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演员来说,都构成了非比寻常的创作压力。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剧中人说了一句什么样的台词/言语,而是他(她)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者是什么在驱使着推动着他(她)们这样说。与此同时,在言语的表象之下,又该如何去呈现那些剧中人竭尽全力想要表达的潜台词,那些不曾宣之于口的言外之意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想要达到这样的舞台效果,需要的是演员内心丰富到极致的情感支撑。“短暂的静场”“静场”“长长的静场”,“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所有这一切舞台提示,加上那些宣之于口的言语,共同构成了福瑟台词的节奏感与音乐性,织就了一张细密繁复的网,令剧中人深陷交流无效与挫败的困境,无法停驻但也无法离去。舞台上的世界,偶尔被言语照亮,但更多的时候晦暗脆弱,如此迷雾重重又不堪一击。每每令剧中人的生活深陷泥沼,无处遁逃……
在静场之外,还有重复。读者和观众们往往不理解那些重复出现,或是乍看变化很小却反复低徊的台词的用意。殊不知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中日常对话的典型状态,每一遍的重复,其实都隐含着不同的情绪。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复调般的音乐美感得以彰显,而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幽微细腻之处,也得以被生动描摹。克制与张力,极简与极致,在作家的笔下达到了完美平衡。对参与福瑟作品舞台创作的艺术家们而言,如何把这大巧若拙的一切精准呈现,始终都是巨大的挑战。
在主题和语言风格所带来的挑战之外,福瑟剧作的舞台,从视觉呈现上来看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灯光,音效,整个舞台设计,对如此独特的福瑟戏剧而言,都太重要了。在福瑟浩渺的美学宇宙中,作家笔下的文字与音乐,与绘画,似乎都能构成跨艺术门类的,交相辉映的宇宙。
最广为人知的当代北欧画家之一蒙克,他画作中的模糊感与不确定性,强烈极致的色彩,或许是福瑟舞台可以参照的视觉谱系。而爱德华·霍普的画面构图,则首先在物理意义上与福瑟剧作存在着相似性:那空旷无人的街道与房间,清晨,黄昏和午夜,都仿佛福瑟的剧中人,也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所踏过的每个角落,走过的每时每刻。很多时候,霍普画笔下炫目的静寂,犹如“震耳欲聋的沉默”,与福瑟笔下舞台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孤寂感极为相似。
写实的极致是抽象,抽象的极致是写实。注目这个空间,当下,过去,未来,仿佛都凝聚在此处;与此同时,却又仿佛空无一物……福瑟的舞台上往往只有屈指可数的人物。他(她)们之间有对话有言语交流,但气氛的压抑却令人觉得人物仿佛永远置身无人的生之旷野。不论他(她)们实际生活的物理空间如何——是悬崖边摇摇欲坠的老屋(《有人将至》),局促狭小的公寓(《夜晚在歌唱》),潮湿颓败的地下室(《死亡变奏曲》),还是人口稀疏的海边小镇(《晨与夜》)……那无人能懂的内心,都令他们终生身处空气稀薄令人窒息的无人空间。
因此,单从画面感上看,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孤独着,渴望着交流却在不断挫败后陷入沉寂与内心世界的暴烈无声……走笔至此,意犹未尽,但天光熹微,或该告一段落。
在文章结尾前,我想要分享的是2012年卑尔根国际艺术节曾上演过的一出来自古巴的《有人将至》。这个版本由福瑟本人在旅途中亲自遴选,在卑尔根当地一位艺术家的私宅中,以环境戏剧和沉浸式的方式得以呈现。演出者在全屋上下三层楼的室内室外空间中游走,时而置身于海风呼啸,没有护栏,一步踏下即是虚空的阳台;时而蜷缩于斗室,展开肉身与灵魂同时短兵相接的对话。而观众们,则可选择或一路追随演出者的脚步;或保持距离,经由在室内多处架设的电视屏幕实时观看演出。
一言以蔽之,福瑟戏剧的舞台呈现,往往因其文本散发的独特光芒与美学印记,让“看福瑟”这件事充满了难度与挑战,也使他的戏剧在商业化的演出市场很难通行四方。摄影大师Paolo Roversi曾说,“光本无形,此刻却有了姿态”,从表面上看,福瑟书写的是生命中的裂痕,但惟有透过裂痕,我们才能看到那丝丝缕缕,穿透而来的光。
谨以加缪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用残损的手掌去抚平彼此的创痛,固执地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命运是对人类的惩罚,而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寄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作者为福瑟剧本的中文译者、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本文标题典出诗人露易丝·格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