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住”“记太牢”是怎么回事
前者是他研究生阶段开展的研究
后者是他回国至今的研究重点
大脑对负性情绪场景或伤害刺激“记忆太牢”
由此会产生一系列认知和情绪障碍
传统的治疗方法无法针对性地“根治”
而他的研究
便是试图找到精准“删除”负性记忆的方法
2020年
他的团队交出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答卷”
成果意外“出圈”
他就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
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伊鸣
从燕园筑梦到负笈求学再到燕归北大
他总是尝试在科研、教学中
以不同的角度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并将自己对科学的纯粹热爱
对科学初心的深刻体悟传递给学生

伊鸣
从临床到研究:他乡遇新知
伊鸣从小最喜爱生物学,但高考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专业。“这是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伊鸣说,在和父母商量并从多方面考虑后,他认为,日后若从事研究,生物学是很好的方向,但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临床医学在打开视角、选择空间方面更具优势,也能在学习过程中检验自己对生物学、对研究是否真感兴趣。
“回过头来看,临床医学的学习经历确实为我日后对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伊鸣说。
考虑到未来可能调整学习方向,伊鸣选择了北大医学五年制,这在当时的医学院校里是最短的学制。
1997年初入大学,尽管发现北医“每一天的课表都排得满满当当”,但伊鸣还是能从“夹缝”中挤出时间,关注着他最感兴趣的领域——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通宵达旦在文献海洋里遨游,伊鸣乐此不疲。随着学习的深入,伊鸣在内心深处愈来愈笃定前行的方向——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继续研究、探索。
从北医毕业后,伊鸣申请到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顶尖学府——伦敦大学学院就读。按照学校惯例,入校后不“分配”导师,学生要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与交流,双向选择确定导师。伊鸣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学校神经科学专业所有教授的主要研究论文都阅读了一遍。“至少读了四五百篇文献,也登门拜访了几位教授。”
当了解到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教授的研究方向后,伊鸣深感遇到“知音”。其研究领域——空间认知和记忆的细胞基础,完全契合自己的兴趣。伊鸣毫不犹豫选择了奥基夫做自己的导师。这位之后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成了打开伊鸣科学视角的“引路人”。
更让伊鸣着迷的,是导师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不走寻常路”的研究方法。“在空间认知领域,有一类以他名字命名的‘奥基夫实验’。这类实验依靠提出问题的独特视角、巧妙的实验设计,用最简单的方法回答最关键的科学问题。在外行人看来,实验者似乎做了一个无比简陋的实验,内行人却能恍然大悟,原来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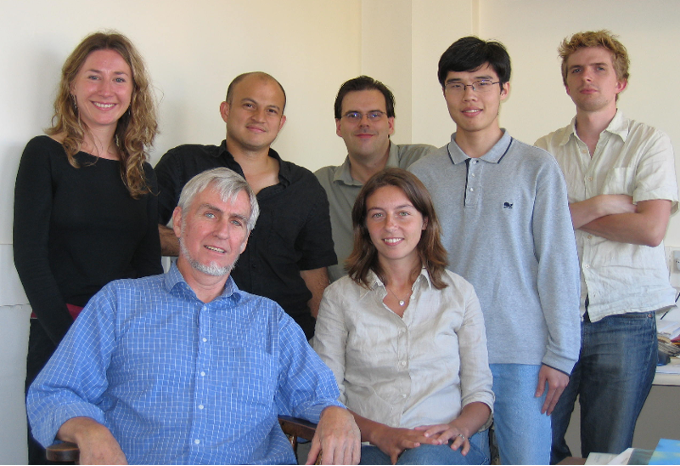
伊鸣和导师奥基夫(前排左一)
从研究到转化:患者需求才是“阅卷人”
2009年,从伦敦大学学院毕业后,伊鸣选择回到北医。当时,他还可以留在英国实验室,或者去其他国家深造。
“我希望用我的所学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尽一份力。”怀着这样的纯粹想法,伊鸣在北大神经科学研究所拓土深耕,凭借学到的前沿知识与研究方法,开启了自己记忆的精准操控与功能重建这个研究方向。

工作中的伊鸣
伊鸣的研究经历可以归结为对两个互有关联问题的回答——“记不住是怎么回事?”“记太牢又是怎么回事?”前者是他在研究生阶段开展的有关海马位置细胞功能特征方面的研究,试图探寻包括阿尔茨海默症等“记不住”类病症的机理问题。后者是回国至今伊鸣研究的重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慢性疼痛等疾病,其生物学机理都在于大脑对负性情绪场景或伤害刺激“记忆太牢”,由此产生一系列认知和情绪障碍。传统的药物疗法往往是单纯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无法针对性地“根治”,还可能作用于其他脑区而发生副作用。伊鸣的研究,就是试图发现“记忆太牢”的发生机制,从而找到精准“删除”负性记忆的方法。
2020年,伊鸣团队交出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答卷”。课题组在两个不同的实验箱里诱发大鼠对箱子的恐惧记忆,进而将基因编辑技术与神经元功能标记技术结合,通过对特定印记细胞群的基因编辑精确删掉大鼠对其中一个箱子的记忆,而对另外一个箱子的记忆完好保留。这个研究为慢性痛、物质成瘾、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以“病理性记忆”为特征的疾病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时很多媒体都对这个成果进行了报道。报道中“删除记忆”等关键词,很难不让读者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神奇想象。
文章发表后,伊鸣在参加学术报告时,总会被问到“你这项研究能不能给人用?”伊鸣也收到很多来自患者的邮件,表达“是否能用新技术抹掉自己的痛苦记忆”这样急切的愿望。
伊鸣深知,实验距离运用到人身上还有很大距离,自己也未曾过多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次成果意外“出圈”,惊讶之余让伊鸣陷入沉思。
“我意识到,从事基础医学科研不能以发表论文为目的,而是充分发挥其实验室和临床之间的桥梁作用,要考虑如何落地、如何真正造福患者和社会。患者和社会所关注的点,往往是研究的风向标。”
伊鸣决定走出实验室,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他开始关注如何让已有成果转化落地的问题。由于有临床医学的专业背景,伊鸣实现了研究和转化的无缝连接,通过与自己医学专业的同学和同事探讨、合作,成果落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最近,伊鸣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专家合作研发的一种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方法进展喜人。该方法基于病理性记忆的细胞机制而设计,在部分难治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探索性应用中收到良好效果,即将进入正式的临床试验。“每个人都会经历负性情绪,但强烈而顽固的负性情绪是一种疾病,对个人和社会的破坏性是巨大的,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伊鸣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专家合作研制的新生儿脑损伤测评工具已获批国家发明专利,也期待能尽快进入临床应用。“脑功能损伤的幼儿如果在三岁前进行正确的干预,可极大改善临床预后。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黄金时期’,则很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乃至一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所以,早期诊断,对孩子、家庭和社会都至关重要。”伊鸣解释。
“只有消除患者的疑虑,减少他们的痛苦,我对这道题目的‘答卷’才能算是真正完成。”伊鸣说。
从转化到参政议政:让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4年初,伊鸣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伊鸣此时还在北京市政协、北京市海淀区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及九三学社北大第二委员会担任多个职务,但他最看重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青工委主任的工作。借助这个平台,他不再是一个人,而可以和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通过参政议政,更有力地推动与民生相关的科研成果和设想扎实落地。
民主党派工作的经历,给了伊鸣一个以不同视角看待问题的机会。伊鸣的提案,都是在实际科研和产业化工作中的深刻洞察,他希望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扫除成果落地过程的种种障碍。

伊鸣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议上发言
当前,伊鸣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让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落地,尽早进入医疗机构造福大众。202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伊鸣对北京市医疗器械进入医疗机构过程中的“堵点”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通过施行顶层设计、一条龙落地服务等一系列政策,畅通“样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该建议得到了北京市主要领导的批示,并在4月17日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中,以多条举措的形式予以体现。
“体制机制顺畅加上政策利好,就能让实验室的成果快一点来到百姓身边,这是我的最大希望。这个过程越顺利,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也越高,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老百姓受益也越快。”
“没有在九三学社和政协的工作经历,我往往意识不到真正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复杂性,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而没有科研和产业化的工作经历,没亲手‘解剖过麻雀’,我也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伊鸣说。
课堂背后的神经生物学原理
“今天进校门的时候,保安小哥拦住了我,问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答道:‘你问得好,我今天就是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
这是一次伊鸣在他的“高级神经生物学”课上讲授“海马位置细胞”发现过程时的开场白。
和他的导师一样,在对待讲课这件事上,伊鸣有着神经生物学角度的思考。灌输式教学方式尽管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它“不符合人脑认知和记忆的规律”。伊鸣说。
讲述陈述性和非陈述性记忆的区别,伊鸣一定会在课堂上进行现场实验。如果请同学们记住“8、7、4”这三个数字,基本上几秒钟就能记住,这种针对信息的记忆称作陈述性记忆。但信息学得快忘得也快。但要用手势快速比划出这三个数字,却着实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能熟练掌握,这种动作技巧记忆称作非陈述性记忆,它获得缓慢,但一旦掌握就很难忘记。“如果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表格,考完试就忘记了;但只要他们记得在课堂上做过这个实验,随时重复一下这个实验,知识点能记一辈子。我的课堂就是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让知识在头脑中扎根、在心中内化。”
伊鸣上大学时,国内“灌输式”教学还比较普遍。而奥基夫的课堂没有概念和结论,只有他把自己研究中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娓娓道来。叙事式的教学让伊鸣耳目一新之余,深感震撼——“原来专业课还能这样讲?”伊鸣从没间断将奥基夫的教学理念传授给学生。在备课中,他愈加体会到导师当年授课时的用心良苦。当然,“我的导师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是自己所在领域的开创者,所能参考的材料,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伊鸣笑言。
 伊鸣参加北医教学基本功比赛
伊鸣参加北医教学基本功比赛
伊鸣的“高级神经生物学”课程,与其说是授课,不如说是活灵活现地向学生复现科研先行者们的探索之路。
James Knierim是最早在一个叫做“内嗅皮层”的脑区中发现响应空间信息细胞的科学家,但并未准确描述其工作模式。而Moser夫妇通过改进实验测量手段,才真正明确了这些“网格细胞”的特征性工作模式,最终也因此发现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奖。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讲这段故事时,除了称赞Moser夫妇对实验细节的敏感捕捉外,伊老师对James Knierim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仅看结果,Knierim教授似乎与重大发现失之交臂,是个‘失败者’。但伊老师告诉我,科学界不应该是‘成王败寇’,重要的发现永远以拼拼图的方式完成,正是前赴后继的科研者不断填补数据与结果,才最终得以呈现其全貌。科学家不应该只一味地追求研究的结果,更应该享受研究的过程。”伊鸣的学生、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的马龙雨说。

伊鸣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述科幻电影和小说里关于“操控记忆”的情节
上过伊鸣课的学生都有一个感觉——“学得爽”,伊鸣善于抓住同学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故事“情节”本已引人入胜,伊鸣还将语言艺术以及对课堂节奏的把握,运用到极致。“教学设计的最高水平是课堂伊始留一个悬念,把所有人的兴趣提升起来,中间不断铺垫,把悬念保持到整堂课,下课前‘抖包袱’,像说相声一样。”

伊鸣与学生交流
王佳昕如今在伊鸣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在她眼中,老师课上的每一个例子都是精心设计的“谜题”。“在讲到空间认知时,伊老师以熟悉的校园为例,不断启发大家思考进行空间移动背后的神经机制,每当一个答案在脑海中闪现时,同学们的脸上总会流露出‘顿悟’的微笑。”
“任何工作做到极致,都可以成为艺术。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课堂教学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伊鸣说。
回归科学初心
为兴趣而研究、实实在在解决理论和应用问题,在伊鸣看来,是科学研究的初心,老师要做的就是让学生保持这颗简单纯粹的心。
王佳昕博士阶段在伊鸣指导下开展研究的时候,真正感受到了这份纯粹。“伊老师尊重每位同学对科研方向的选择,鼓励大家去做感兴趣的课题,我们只要纯粹地做科研,不用考虑科研经费,不必顾虑人情世故,更不用担心课题进展不下去该如何收场……伊老师无论背后顶着多大压力、付出多少精力,从不与学生提及哪怕一点。”
“发表论文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半路产品’,千万不要把它当作终极目标。现在找工作、评职称需要它,这是现实,但它依然不是也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伊鸣强调。
伊鸣正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伊鸣不遗余力实践着这个理念。基于问题的学习(PBL)课是北大医学的一个教学特色。老师在课上给学生展示典型病例,同学们自主查阅资料、讨论,一步步跟着病例的诊疗信息学习相关知识。每个病例进行到最后,老师都会对其总结,点评大家的学习成果。
每当此时,伊鸣就结合他在政协履职中的独特经验和开展成果转化工作的经历,分享新的观点,将话题延伸、发散。如一次在对阿尔茨海默症病例进行总结的时候,伊鸣借此“切入”政协视角。他曾在2023年北京市政协一份调研报告中执笔了养老与安宁疗护部分。他用第一手资料向同学们介绍国内老龄化问题及养老现状。
“医学生可能会认为在医学院学习的是诊疗技术。但事实上,真实的医学要复杂得多,不是摆弄机器。对一个医学问题,医生、研究者、患者、家属、企业、政府及管理者都有各自的视角,他们组合在一起才是医学真正的样子,否则都是盲人摸象。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讲述更多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内容,激发学生从多个视角、全面考虑问题;也让他们认识到,解决问题才是科学的根本,拓展视野,为的是回归本心。”伊鸣说。
“在科研中无论遇到多么棘手的问题,伊老师总能以最简单、最漂亮的方式加以解决。”王佳昕体会颇深的,是伊鸣一次次带给同学们的惊讶。这也是伊鸣当初看到导师奥基夫“庖丁解牛”般地将纷繁复杂的问题从容拆解时的那份惊讶。
伊鸣希望他的学生能将这份“惊讶”保持下去。
“每个人都有盲点,惊讶源于发现自己的认知盲点。不断发现并突破这些盲点,才能持续进步。”伊鸣说。
人
物
介
绍
伊鸣,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记忆的精准操控与功能重建。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青工委副主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兼市委青工委主任、九三学社北京大学第二委员会副主委等职务。研究成果曾获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多次获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医学(医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特等奖、北京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北大医学部教学优秀奖等殊荣。
“燕归来”系列报道
聚焦选择北大的优秀归国青年学者
他们的鲜活故事折射出北大校园文化精神
生生不息的脉络传承
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大人那份独具的追求卓越
报效家国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