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吴海云
1984年,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王陵区,考古队正在挖掘一座编号为M259的小型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二层台上发现了14枚成年人头骨,其中一枚盛放在一件铜甗中。尽管甗是一种蒸食物的炊器,但考古工作者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联想,只觉得人头可能是偶然掉落进去的。
时间到了1999年,在距离殷墟王陵区不远的刘家庄聚落,考古人员在发掘编号为“刘家庄北M1046”的贵族墓葬。他们在该墓的棺木右侧发现一名少女的无头尸骨,原本属于人头的位置有一个铜甗,里面盛有她的头颅,头骨的颜色灰暗,说明它曾经被蒸熟过——直到这个时候,考古人员才愿意正视铜甗和人头之间的联系,并不得不对商朝有了新的认识。
这个故事仿佛是一个隐喻: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意去承认或深究历史深处的黑暗,哪怕活生生的证据就摆在眼前。尽管商朝存在人祭行为是一个不算冷门的知识,尽管这些年去殷墟参观的游客们都曾目睹过那层层叠叠的人祭坑中累累的白骨,但对于人祭,人们似乎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那是一个黑点,尽管并不光彩,但也微不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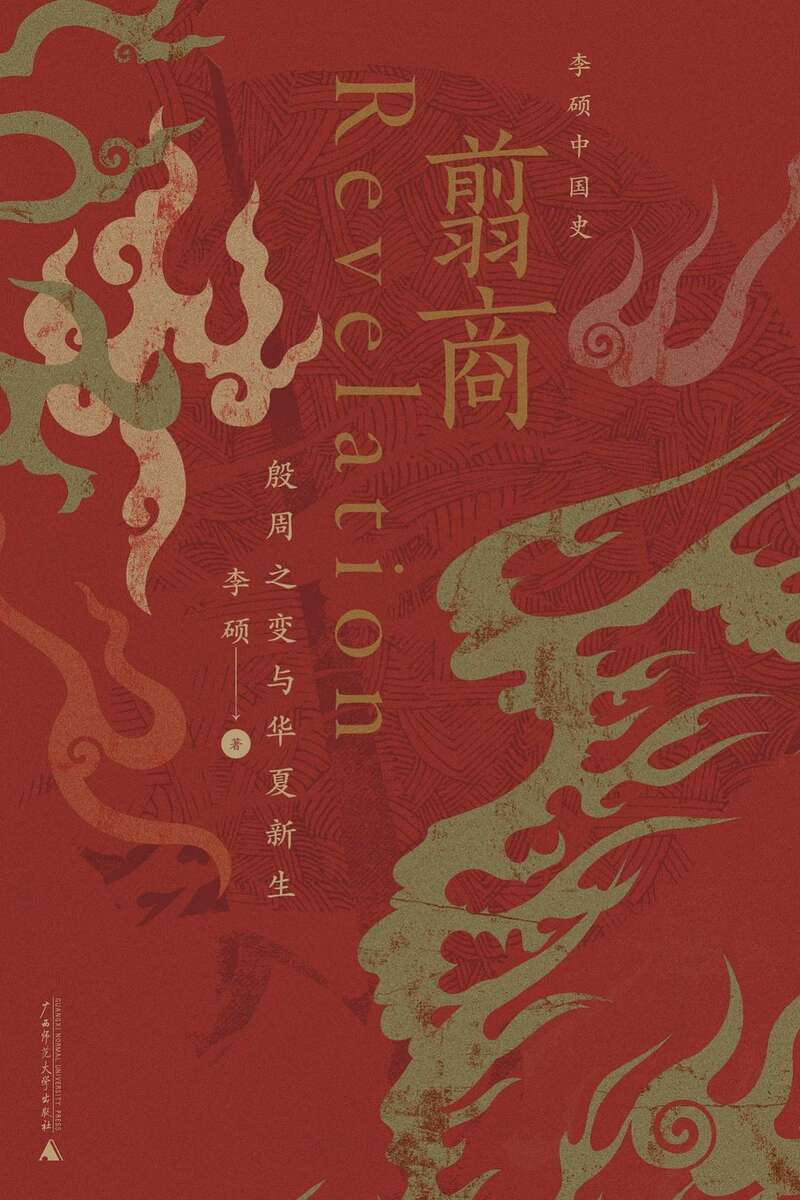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影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影
然而,万一人祭并不只是一个“瑕不掩瑜”的小黑点,而是商朝的一个重要特征?万一这种行为其实是商朝王室的统治方式,以及一种由上而下的全民实践?——这是2022年10月出版的、由青年历史学家李硕所撰写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所带来的信息。
其实,相关信息早在十年前就曾经引发热议。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李硕写了一篇名为“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长文;文章先是发表在著名杂志《读库》上,之后又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多年后,已经出版过《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等作品的李硕将那篇长文扩展为一本47万字的历史类非虚构作品。许多读者的感受就像考古学家许宏在推荐此书时所说的:“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
李硕
《翦商》的前半部分,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系统而细致地阐释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发展: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六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被一些人认为是夏朝旧都的二里头文明也沿袭了这种风俗;而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把它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个崇尚暴力的民族,在他们所创造的“甲骨文”里,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在商朝开国百年左右,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让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和统治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殷墟遍地都是殉葬坑和献祭坑。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鬼神喜怒无常且干预人间事务,需要时时向他们献祭生命才能获得福佑;不仅如此,这些统治者还可以通过献祭野蛮的异族人,区分出“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人),由此构建族群的认同,这种国家祀典同时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经常举行人祭;从北境的军营到西境的前哨基地,各地的商人部落都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通过对于大量考古资料的文字还原,作者将三千多年前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呈现在了读者眼前,比如——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在书的后半段,作者开始讲述这种残忍的制度是如何从历史中消失的。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人祭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作者将人祭风俗的消亡归因于周朝几位开创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
在作者的阐释中,由于人祭的体制化,商朝统治者不得不长期维持对异族(通常被称为“羌人”)的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在此过程中,原本也属于异族的周人投靠商朝,成为其王室在关中地区捕猎人牲的代理人。在商纣王统治期间,被后世称为“周文王”的周人方伯姬昌被抓到殷都,目睹了人祭的残忍场景;更可怕的是,他的嫡长子伯邑考还被商纣王用于献祭。在从殷都侥幸逃出后,姬昌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并开始用这种占算技术谋划他的“翦商”大业。
在姬昌去世后,他的儿子、被后世称为“周武王”的姬发在公元前1046年发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纣王。然而这个时候的姬发已经被商王朝的血腥同化,就在伐纣成功后不久,他就一次性向上天献祭了两百多名商朝贵族和官员。不过,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就死去了;而他的弟弟、被后世称为“周公”的姬旦要比他温和得多,从某种意义上也强大得多。
周公在摄政期间迅速禁绝了商王朝残余势力的人祭行为,并将与人祭相关的文献记录——包括周人曾为商朝四处征伐猎捕人牲的耻辱历史——尽可能抹去。周公还编写出一套以“天命观”为代表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指出王朝要获得上天的保佑,需要治民的德政,而不是向神明杀戮祭祀。五百年后,孔子盛赞周公所开创的礼乐制度,并通过他本人开创的儒家学说,卫护周人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主义立场。
作者指出,“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周公对于商朝人祭制度的消灭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直到殷墟在上个世纪被挖掘发现,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陆续出土,真实的商朝往事才再度浮出水面。
记者采访了李硕,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经过,以及他的历史观和创作观。
【对话】
澎湃新闻:《翦商》这本书是从你在2012年写的那篇“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文章扩展而来的。请问这当中为什么隔了那么久?你当初又为什么会写那篇关于商朝人祭制度的文章?
李硕:商朝的人祭制度,尽管社会公众知道得不太多,但在学界并不是什么新闻。毕竟,殷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考古发现,之后的每一次挖掘都会发现新的人祭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比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王平、顾彬的《甲骨文与殷商人祭》。我在读书的时候,就了解到了这些知识。
真正让我想写一篇东西的,是一部美国电影——梅尔·吉普森的《启示》,故事背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制度。这部电影让我感觉特别震撼。我看完后就想,哎呀,人家好莱坞可以把人祭拍得这么好,拍出了那种真实的、原始的、茹毛饮血的感觉。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啊,怎么就不能写出来呢?于是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你当时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专著?
李硕:想过的,但当时我在忙博士毕业的事儿,之后又是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又有许多科研和教学任务,因此一直没有时间去写书。但我一直想,文章已经在那里了,如果有其他学者把这个素材写成一个非虚构作品,或者写成像《冰与火之歌》那样的纯虚构的作品,我会觉得非常开心。但好几年过去了,我所期待的并没有发生。
2020年初的时候,我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变动。我工作的地方——新疆乌鲁木齐开始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而我的女儿在成都出生了。于是,我辞去了在新疆大学的工作,回到成都和家人在一起。因为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我有了一个窗口期,于是就开始写那本我早就想写的书。我没想到一写就写了整整两年。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很期待有其他学者把这个故事写成非虚构类作品,但没有人这么做,最后只好自己来写。这让我想到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历史悠久,有太多可以讲述的故事和素材;但另一方面,面向公众的历史类非虚构作品又是很稀缺的。这是为什么?
李硕:我想这首先是专业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身上的任务太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写非学术类的作品。你看我在新疆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写《翦商》。
另外我觉得,很多历史学者可能在写作方法上需要开一些技巧和“脑洞”。你看我们现在一些很有名的学者,也擅长写一些面向社会读者的学术随笔。但在这基础上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样,讲出一个独立性的故事来?这一步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学者大多都没有相关的训练和类似的创作经验。
澎湃新闻:那看来,你创作《翦商》的过程,也是你在摸索这种历史类非虚构写作方法的过程?
李硕:是的。我可以参考的东西不多,因为国内同类的作品很少,所以我主要借鉴的是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失落的文明》那一套丛书,尤其是学习这套书通过考古现场复原历史的写法。
澎湃新闻:你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人祭是商朝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下这样一个论断是需要勇气的,不是吗?
李硕:还好吧,我们对于上古历史的认识本来就是在不断更新换代中。原先,中国人熟悉的是那套西周创立的历史观,好像上古时期都是三皇五帝,都是圣贤,如果一个王朝出现了一个暴虐无道的君王,那上天就会让人间改朝换代。那是一种总体而言温情脉脉的历史叙事。
后来,我们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五段论,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脉络。在这样的框架下,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但是,商朝真的符合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那个奴隶社会,信息来源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那个社会的奴隶主要是指一个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劳动力;然而商朝的所谓“奴隶”,主要是被拿来献祭的异族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人类古代文明彼此间差异还是很大的。以前学术界最熟悉的是欧洲史,现在,各种古代文明的考古知识都积累得比较多了,可以进行很多对比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总体而言,对于商朝,我们的了解和认识还很不充分。除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商朝还有着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有着规模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设施,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的诸多层面。研究者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澎湃新闻:但是你的重点放在了人祭上。书中的许多内容简直残忍到不忍卒读。当你在还原那些血腥场景的时候,你的主要感受是什么?
李硕:当然是非常难受的。就像我在后记中写道的,写这本书是“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而且这不仅仅是直面历史“深渊”的恐怖;我意识到人性其实在本质上没有变化。你从商朝祭祀坑遗址得到的启示就是,人类有时候就是幸灾乐祸,就是喜欢看到同类受难,而且遭受苦难的对象和他的相似程度越高,他就越兴奋。
澎湃新闻:我大概可以理解这种直视“深渊”的痛苦。那你在研究和写作这些资料的时候,是靠什么支撑住自己的呢?
李硕:那可能是因为周文王家族的故事。他们带来了希望和变化。我带着这个故事去和考古的资料结合,才有信心写出一个比较系统的东西。如果只是写人祭,写杀杀杀,那我可能无法写出一本专著。
澎湃新闻:既然提起周文王,我想和您讨论一下书里的一些细节。你在书里对周文王的《易经》做了全新的解读,认为《易经》是周文王用自己能看懂的语言体系写成的“黑话”合集,其中有他带领周人俘获羌人并进贡给商王朝的内容,有他在殷都目睹的人祭场景,甚至还包括伯邑考被献祭时的细节。这种对《易经》的解读是否受到了很多质疑?
李硕:我的判断是,周公有意识地消除了绝大部分关于商朝人祭制度的文献资料,但他不敢动自己父亲的作品,只是对《易经》做了重新诠释,形成了后世熟悉的《周易》。而在原始的《易经》中,确实藏有和人祭制度有关的诸多信息。
话说回来,对《易经》的研究本身就是百家争鸣、至今没有任何定论的一个领域。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怎么用来算卦?对此的共识非常少,大家原本就是各说各的。现在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易经》的著名学者,是美国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翦商》这本书,我很期待他的反应或批评。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兴趣,你所讲述的这个历史故事,最后的主人公是孔子。这是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安排。请问你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关于商周之变的历史故事最后落到孔子身上的?
李硕:这个故事最后落在孔子身上,在逻辑上是顺畅的。因为是孔子整理了周公的理论成果,编撰了儒家的“六经”,而后世对于上古时代的了解基本上都是通过“六经”。换句话说,孔子决定了我们对上古时代的认识,这个历史角色确实是非常特殊的。而孔子又是商王族的后裔,他和商纣王有共同的祖先,这种身份肯定会让孔子思考很多东西。
我们传统对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叙事,都是周公和孔子奠定的,看上去都比较低幼,适合讲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但周公、孔子本人所了解的上古史肯定更残酷、更真实,是原装“成人版”的。他们故意隐藏了某些史实,重新杜撰一套温情的上古史。借助考古,我们今天能够找到那些被周公、孔子藏起来的真实历史,至少能复原一部分。
澎湃新闻:你笔下的周文王、周公、孔子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但在阅读的时候我也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个体的努力是决定性的。这会不会有点精英主义?您觉得历史真的可以被极少数的个体精英的努力扭转吗?
李硕:我也不想这样,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我们研究一段遥远的历史,史料只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东西,也就是大人物们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有其他史料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比如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作用更大,那我们也可以写出另一套史观的东西。
另外,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东西确实就是一些大人物在其位置上的产物。那当然不仅仅是乐观的东西,也有很多悲观的东西。
澎湃新闻:无论如何,你写了一个非常饱满而自洽的历史故事。这会不会坚定你做一个全职作家的信心?
李硕:这倒不会。我已经联系好了下一份工作,应该不久后就能上班了。并不是我不想专职写作,实在是因为写书无法养活我。比如说这本《翦商》,市场反应已经比我预期得要好很多了,但从写书到出书周期很长,平均算下来一年也没几万块钱,没办法养家糊口。
当然,如果我会写那种纯虚构的历史小说、成为一个马伯庸那样的畅销书作家,情况会好一些,但我又没有那个能力。其实在2019年,我曾想把商周历史写成小说,因为那时看了个美剧《高堡奇人》。这片子的格调非常阴郁、灰暗,我觉得和周文王家族的故事风格特别像;剧中的一位日本老者,频频求助周易占算,在我眼里就像是地窖里的姬昌。我那时还向当影视编剧的朋友请教,怎么写文学作品,但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不行。我想象力的翅膀已经被我所受的学术训练捆住了,只能像侦探破案或者法官断案一样,在充分的证据上形成推论。不过还是得感谢《高堡奇人》,它是《翦商》这本书的药引子。
澎湃新闻:那你还会继续写下去?
李硕:会的,我还是会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写书。我曾经吹过牛,说要写一套关于中国史的书,现在殷周之变写完了,我想接下去写西周和春秋,最好能一直写到唐朝,这样就基本把中国历史的“古典时期”都涵盖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写到唐朝就结束?
李硕:唐是诗的时代,而诗,是汉文明中富有宗教性的东西,它不需要提供创世纪或诸神的谱系,就能让人获得“超越性”,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如果我能写到、写好唐朝,就足够了。
我下一本书不会像《翦商》这么“重口味”,市场反应肯定不会太好,但我相信我还是能写出一些大家目前还不太知道的东西。因为我对历史的理解往往和现在学界的基本认知很不一样,但这种尚不成形的思维很难用语言完整表达,所以只能慢慢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