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式的考研迁徙是一年一次无比壮观的社会性运动。每一个个体都奋不顾身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大家勤奋地背诵,疯狂地学习,搭乘着绿皮火车、长途汽车、手扶拖拉机向中心城市进发。
以考学的方式解决户口迁移,是当时普通人改变生活环境的一条捷径。当一个人拿到了盖着红色印章的录取通知书,就可以顺利地跨越各种繁琐的行政手续,奔赴你向往的城市。
我决定走考研这条路,而目标城市只有北京。
# 选择 #
最终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一个险招儿,因为当时对这所学院的认识多来自设计杂志,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的作品经常刊登于此,尤其那一些画工业设计草图的,简直帅呆了。齐爱国老师的手绘汽车效果图算是那一时期的巅峰之作,寥寥数笔就勾勒出现代化交通工具简洁利落的造型;再有就是何镇强老师的旅欧淡彩速写,在崇尚表现阶段的建筑学不啻于高山仰止,掀起了模仿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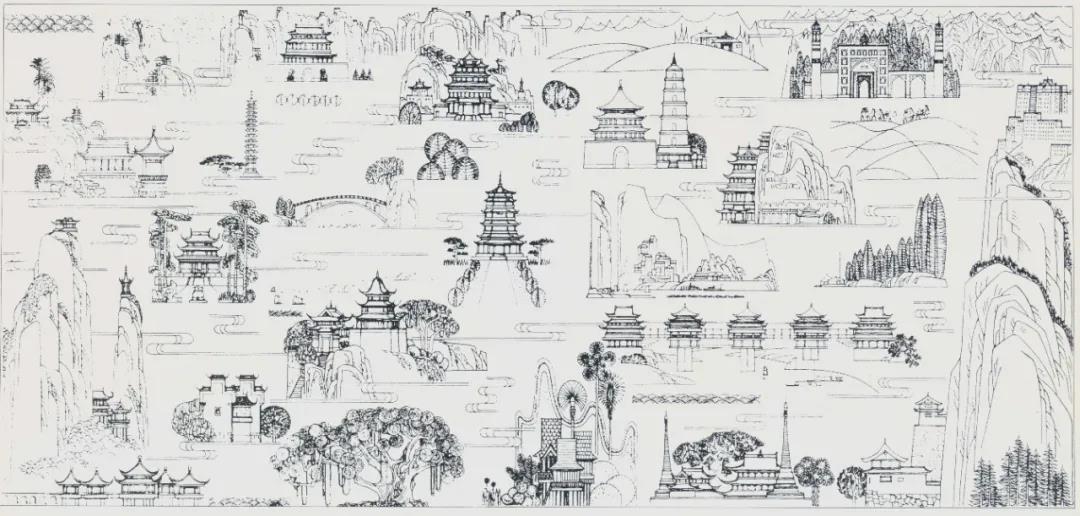
我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与我从事的工作方向紧密相关的专业就是环境艺术设计,这个专业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建筑设计和艺术创作在环境意识的作用下,不断交融所形成的一个新的学科。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恰逢该学科高歌猛进的开始,理念的系统化、工作方法的规范化正逐步成型,为了应对社会发展所进行的扩展也蓄势待发。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是这个学科最有活力的一个阶段,建筑界、艺术界的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都热衷于这个话题。“环境”是一个新的观念,是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过去的建筑设计和建筑装饰;同时这样的设计活动,它还填补了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盲区,为设计和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而且这样的学科对于解决中国正在进行中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个专业的迅速崛起在当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期望。
在确立目标之后,我就赶赴北京去找在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校友王阳,了解考研具体要求。
很小的时候,我的其它功课一塌糊涂,但是却喜欢涂鸦。家长曾经一度希望我去尝试发展绘画特长。我在小学期间看过出自该学院张光宇先生笔下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初中时看到张仃先生的《哪吒闹海》;高中时期,我模仿过吴冠中先生的速写,尤其是他笔下早春二月生机勃勃的柳枝让我着迷;读大学本科以及留校任教期间,也听说过首都机场壁画,由此知道了袁运甫先生、祝大年先生的大名,何镇强先生的建筑速写更是令我钦佩不已。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需要在精神上接近这个学院,进一步了解它。

# 踩点 #
在北京站下车之后乘9路公交车大约四站路程就到了东三环北路34号,也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校址所在地。
当时的东三环外侧基本上就是一个农田和工厂混杂的郊区,北汽、北客、电缆厂、3501、内燃机厂、热电厂等都在这一带,到处都是大厂房和烟囱,而国际贸易中心已经傲然屹立在东三环内侧了。

中央工艺美院的主楼,是一个不算扎眼的、带有中西混合风格的、有几分装饰的四层红砖建筑。它安详地躲在林荫道东侧临街小花园的后面,窥视着门前的车水马龙,气定神闲的模样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深厚的的功底,一副坐怀不乱的样子。
其建筑的风格属于“新而中”,平屋顶的出挑深远,虽是现代主义的做派,但其檐口厚重并依稀贴挂着少许纹样;建筑主体使用的红砖具有工业化和平民化两种气质。入口处雨檐依旧厚重,凭借一组醒目的红色不怒自威。那是一组漆成红色的木门,仿制中国传统建筑门扇的经典做法,并大胆套用了宫廷中的小木作纹样。

顺着台阶拾级而上,那组红门的正中央的两扇半虚半掩,像一个古典园林的入口,但是红门的背后是黑漆漆的过厅,显出几分神秘。中央工艺美院入口处的环境意象值得玩味,它透出一种行政、教育、园林混合的气质,也是中式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谨慎的联姻,既含蓄、典雅,又有几分威严。
面对这样的风貌和空间格局,外来者总会临时性地陷入一种脑供血不足的状态之中。站在那寂静的台阶上,面对着这虚掩的大门,似乎是面对着一道哲学性的问卷,“何去何从?”。
两位和蔼的门卫倒是没有问我“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性问题,待我和他们说明了进校事由和联系人的部门、宿舍门牌号码之后,得以走进这个神秘的建筑群。这是一个女生宿舍和行政办公混杂的综合楼的门厅,穿过这个过度性空间后就是一个豁然开朗的院落。那个出口处正对着的一个水刷石的圆形花坛里,姹紫嫣红,花儿们此时开得一塌糊涂。由于正值暑假,整个校园难得看到个人影,一只老虎斑纹的野猫,大摇大摆地从前方十几米处走过,拐了个弯就消失在右前方自行车车棚的凌乱之中去了。知了们就更显放肆,它们的齐唱占据了这个空间。
找人的时候我误打误撞,敲开了学生宿舍、教室、研究机构三种不同类型空间的房门,看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学生宿舍里,一个身形高挑,面色白皙,并戴副眼镜的青年掀开门帘露出半个身子,与他一同扑到我面前的还有一股强烈的松节油的味道,创作状态中的人总是显出少许的木讷;专业教室里,几个女孩子在画那种大幅的丙烯超现实绘画,凝神静气地在用极细的笔和喷枪死磕那些工业废墟里的破败细节,商业环境里的光怪陆离;环艺所里则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复印的、制图的,使用喷笔喷绘的,忙得不亦乐乎。校友王阳指着其中一位微弓着腰,神情专注,左右手各执一支画笔的青年人对我说,此人可以左右开弓同时画两幅效果图……

# 恶狠狠地背诵 #
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踩点”回到哈尔滨之后,我抽出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再小心翼翼地拿出1988年的考研试卷,掐着时钟,严格按照考试的时间做了一遍测试。令我万分失落,28分就是我那次自测的成绩。我深知要想突围成功,也就意味着在距离考试四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刻苦的学习,每个月必须要提高10分左右。

回顾人生,至今这个英语考试攻坚的过程,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为骄傲的事情之一。我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在囚室里偷偷挖地道的越狱者,也像一个手执小镐日夜不停地挖掘横亘在面前的这座“大山”的新时代愚公。
我对每日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规划,精确到了10分钟的度量单位,几乎将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开会之余的所有时间都倾注到了背英语单词,做练习题上了。我几乎把一本厚厚的专用于考研的辅导单词、词组汇编,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内容全部背了下来。大概每过10天,在经过新一轮奋不顾身般的背诵和学习之后,我就会掐着钟表,躲在小屋里按照考试的规则进行一轮自我测试。那分数的变化简直像是蜗牛爬山,像极了东北的大秧歌,歪歪扭扭,步履蹒跚地前进三步后,往往会向后退却半步。但我并不气馁,而是横下一条心依然每天拿出五到六个小时来学习英语。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又艰苦的拉锯战后,奇迹终于显现了,到考试前一个月我自测的成绩基本上稳定在了六十分左右,离考试最近的一次自测分数甚至还达到了七十分。
除了埋头死磕,我还上了英语补习班,辅导老师是英语教学的权威杨匡汉教授。杨教授广东一带人士,口音很重,但讲得很好,从容、淡定,还有一丝幽默,他深入浅出的讲授令我茅塞顿开。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才知道对于学习了十几年的英语自己几乎是一个白痴,从语法到音标再到听力可谓千疮百孔。我经常想到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那句话:“今晚的月亮格外明亮,我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的二十几年都是发昏。”耐下心来之后,原本欠缺的储备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构性的缺失部分也得到了补救,心里的底气俨然又增加了一分。
从1991年开始,硕士研究生英语考试中加入了听力的内容。我买了一款当时最先进的半导体收听英语新闻。像块板儿砖一样沉甸甸的黑家伙从广东一带寄来,每天背着它,有一种全副武装的感觉,我决心要用这块板儿砖砸开英语考试的大门。
和英语惊心动魄死磕的几个月里,我无法改变它,却在不断接近它。我让那厚厚的辞典搁在我最贴身的地方、随身携带的拎包里、餐桌上、枕边......神奇的是它竟然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我,一度我几乎背诵成瘾、流连忘返了。
# 赴京赶考 #
终于到了临近考试的时间。为了适应考试环境,我提前一个星期来到了北京,住在了位于朝阳区南湖渠的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的宿舍里。
考研的那几天,为安全起见我都选择了自己骑自行车,冒着严寒从南湖渠到光华路,骑行时间大概需要1个小时。开考的那一天早上,南湖渠一带农家的鸡还没叫,我已精神抖擞麻利地起床,吃完早饭准备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借着路灯微弱的光芒骑出了那一条狭窄的乡间公路之后,灰蒙蒙的天空的东方开始呈现出鱼肚般的白色。再从京顺路拐上三环之后,天已经完全放亮了,正在施工,体量巨大的燕莎中心,几何形状明确的亮马桥大厦,包裹着亮晶晶的玻璃幕墙的长城饭店一个个从身边擦过。路过庄严伟岸的农展馆时,不知为什么心情突然豁然开朗了起来,而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苏醒,宽阔的大街上,车辆来往穿梭,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也多了起来,混迹于这股洪流之中,抒情无比的《北京颂歌》仿佛在耳畔响起。
研究生考试的考场设在教学楼一楼东侧,第一门考试科目就是英语。铃声响起之后,长时期因紧张和专注积聚的负能量爆发了,它来得如此猛烈,令我手足无措。只是觉得刹那间大脑里一片空白,考试开始后的前十分钟内根本无法进入读题的状态,于是自己连续做了十几个深呼吸稳定下来情绪,就这样才缓慢地进入了考试状态。结束考试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居然还有10分的题没有做,这是我半年来所经历的模拟考中从未有过的事情。我想是由于过度紧张导致的状态失常吧!
当我进入专业考试时,明显就顺利了很多。专业考试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一整套的图纸专业设计。做设计师工作的杨志刚同学,顶着压力给我提供了他们合资公司最先进的绘图工具,其中最关键的是两套进口的马克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灰色。如果使用水彩或水粉,灰色是最难调的,而且还需使用电吹风让图纸快干。使用马克笔,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当我把那一套堪称华丽的工具铺陈展开以后,马上吸引了整个教室中所有人羡慕的目光。读题、构思、草图、起稿、着墨、上色、写说明,最后是整个图面的修饰和调整,我的计划几乎精确到了分钟,绘图的进度遥遥领先。
在最后进行的面试环节,我见到了参加这次考试的所有竞争者。那一年环境艺术设计方向只有一个硕士招生名额,导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张绮曼教授,而15位考生全部来自中国著名的建筑院校和美术院校,其中建筑院校更是几乎“老八所”全部到场。考生们个个都踌躇满志,但此时的我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自己将作为一匹黑马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