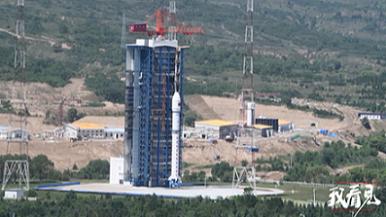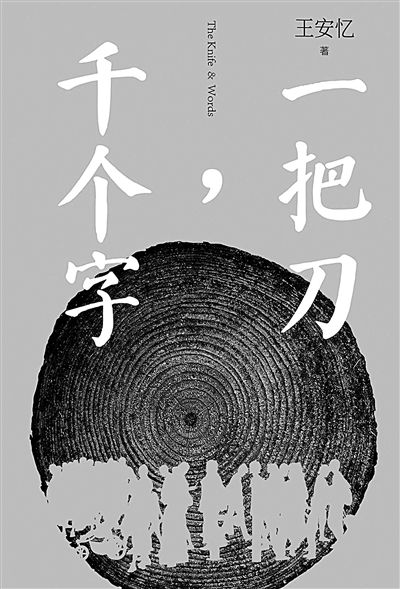
去年,有出版社全套完本出齐了毛姆短篇小说全集,厚厚四大本,看得格外畅快。其中不少都是写他那些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事业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同胞。人如树,皆有根,移植别处后,不一样的风水总会滋长出些不一样的风貌与气质,于是许多篇什堪称光怪陆离妖异魅惑,犹如“洋聊斋”。看的时候就想,中国人现如今也是开枝散叶,全地球凡有井水处即有我同胞,缘何不见中国的小说家好好写写这些人呢?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把刀,千个字》就来了。
他是纽约法拉盛的一名厨师,陈诚。
1
小说的名字从一句俗语与一句诗化来,“千个字”是袁枚的“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而扬州人谋生向有所谓剃刀菜刀修脚刀“三把刀”之说,而主人公陈诚用以安身立命的,正是一把菜刀。
先看张新颖老师写的故事梗概:“以一位淮扬名厨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他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古人道,礼失求诸野,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后来在纽约法拉盛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
——里弄城郭,上海乡下,南方北方,中国美国,东方西方。
烟火气,屋漏痕,里弄仍是这一切的起点。王安忆永远是从上海出发的,作家的笔如桨,总是以此为支点为踩石,一点点地挪移、摆荡,然后进入更豁达更开阔的地带,然后开疆拓土越游越远,这一次,游到了大洋彼岸。
王安忆于我个人,是真真正正的陪伴型作家,看完《一把刀,千个字》以后,试着去找《69届初中生》的单行本,这是我读的第一部王安忆,说起来,那已经是高中时代的记忆了。书到了之后,马上翻找我三十年后依然记忆清晰的情节——经历千辛万苦之后,雯雯回城的所有手续都办妥帖,任一累瘫在床上。一路波折太多,遂心后反而不是开心,而是带着三分失落三分怨愤,闹了一会儿之后,两个年轻人都波涛汹涌地哭了。
“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没法子把这地方变成上海,可我们能够回上海去,我们从小在那里生长。”
雯雯呜咽着,他们的眼泪交流在一起。于是,一切便在这交流里冰释了。
——从那时到现在,王安忆一直不停地写啊写啊写啊,中国还有比这更勤力的作家吗?反正我是想不出。她的创作能量简直到了骇人的程度,放眼望去,好像也就是日本的村上春树和土耳其的帕慕克有的一比。她最擅长书写的,也永远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他们在命运的河流里载浮载沉,顺应臣服的同时又有本事一直保留着自己内心那个核芯不被碾压到崩解,所以,到头来,一个个反而有一种悠游甚至高贵的气象。无论是松江府门第人家的女眷,还是时代大变动中的“淑媛”,又或者是迷迷瞪瞪的女囚阿三、小区门口的小皮匠、在人家帮佣的富萍……现在,这个人物序列里又多了一个手执菜刀的淮扬菜名厨。
2
陈诚是男一号,但说他是辗转于妇人之手也不为过。小说写得最生动的,也是女人。
在这女人的群像里,我以为写得最好的是他的嬢孃和他的妻子师师。这两个女人,一个冷冷清,一个热扑扑,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个敏感又怯弱的男孩/男人代行母职。
嬢孃看起来是某种典型的上海女人,精明,孤傲,有时心肠狭小,当她看到在乡下度假愉快到忘我也忘了她的小男孩时,那几分强压的嫉妒和不悦写得实在精彩。但也是这个女人,在局促的亭子间里用斤斤计较的精打细算,用捉襟见肘的匮乏努力喂养和照料着这个被抛掷在时代巨轮侧畔的幼侄。
庸常与凛冽、促狭与大度,侠义与计较,阴郁与敞亮拧在一起,刹那转换,读者刹那被击倒。
全书中我爱看陈诚和师师的爱情,那算得上是爱情吗?这关乎我们怎么定义爱情。如果爱情必须有那种轻微发晕发烧的眩晕感,那自然不算。他俩的姻缘不过是各有经历的两个旧相识在异国重逢,机缘巧合顺水推舟,但又是奔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长长久久而去的。没有江河湖海的欢腾,更多相濡以沫的温情,当然,也免不了天下所有夫妻都有过的口不能言的“盲猜”:
他们变得生分,明显有了裂隙,越来越宽和深,跨也跨不过。她在心里叫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在心里说: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可是,她那里却保不住了。
这一段真是让人好生辛酸!
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他的妻子,个个眉目分明。甚至那个惊鸿一瞥几乎没有几句台词的、来自越南西贡的华侨倩西,也是三笔两笔便令人惦记:
“互相看见对方无名指上的戒指,意识到有许多事情发生了。”
她和陈诚有没有发生过些什么?如果没有发生过什么,她的小窝何以就成了他的避难所和高压氧舱一般的存在?漂泊的身和烦乱的心要不时躲在那里才能长出继续活下去的力气。所以,他俩到底是怎样的交情?这个默契到底从何而来?作家偏偏大量留白,两个人甚至对话都寥寥,甚至屡屡错身不打照面,更遑论这个那个。可是,又何必非要探个究竟?人间事哪里能样样分明?说得清的只是极小部分,更多的不过是混沌空茫。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3
认识她,他方才知道,世上有一种渴望牺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安稳岁月里,光是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但等特别的时刻,能量聚集,天雷与地火相接,正负电碰击,于是,劈空而下,燃烧将至。
小说用了半部的篇幅写陈诚的母亲,这是王安忆少所涉笔的人物类型,一个为真理而殉难的烈士。
母亲没有名字,可是但凡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很快就知道这个原型其来有自。那位女性的形象一度曾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小镇,对当时年纪尚幼的我而言,印象最深的除了那些骇人的迫害细节,就是她惊人的美丽端庄与文艺气质,特别是一双眼睛,深邃明亮,令人过目不忘,完全合于其时我们对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想象。
时移势易,那个名字如今已几乎不被提起,那段历史似乎也已经彻底翻篇,所以,当我意识到作家写的是她的时候,竟生起一点感激——真好,还有人记得她,这样长篇大论地书写她……虽然与上海里弄、美国华埠的描写相比,这一部分更像是线条的勾勒,写意地呈现,但有人写她,真好。她太稀缺了,不该这样淡出记忆湮没于历史。
4
口味最忌刁钻促狭,淮扬菜,好就好在大路朝天,一派正气,肉是肉,鱼是鱼,不像广帮,听说有吃猴脑的……我们淮扬一路里,绝无稀奇古怪,即便荤腥,也是茹素的荤腥……然而到了沪上,根性大改。
《一把刀,千个字》主角是厨师,食量自然不小,只一个“软兜”——其实就是鳝鱼——就兜兜转转滑滑溜溜地用了不少笔墨,其间也多有妙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微型的“软兜文化冲突学”,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家宴。
看陈诚在美国慢慢起步,开始自己的厨师生涯,总不免会想到李安的《饮食男女》和《喜宴》,一饮一啄,酸甜苦辣五味冲顶;以喜名之,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上头。
陈诚一家是大流散后小团圆,但一张饭桌总是难以安放。没有一次家宴能从始至终保持融融泄泄,每次家宴每次餐聚,几乎都像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暗战。要么是姐姐与师师之间的唇舌暗战(这种时候,在场的男士只好像陈诚一样装聋作哑暗自评弹,或者像美国傻姑爷那样猫三狗四歪打正着),要么就是父女父子之间方凿圆枘般传情失败归于沉默,终于有一天彻底掀了桌——色香味并不能疗愈应急创伤,历尽劫波,依然恩怨难泯。
这一掀桌,就从小日子的微澜带出了大时代的风雨,作品行至下部,陡然换了一副肚肠与面目,从名厨成长史一变而为英雄母亲的牺牲。
中国古人早就用“调和鼎鼐”来比喻治国,又用“治大国如烹小鲜”比喻治理之道,想来是深谙烹煮不易调和艰难。看来,小道中孕育着大道,向来如此吧。
5
“她的真理在星空,我们的,在日复一日之中。”
烈士是在星空翔舞,厨师则是在烟火中消磨,两代人之间,以大时代的怒潮接驳着小日子的微澜。
《一把刀,千个字》写母亲的部分显然不及写陈诚、写师师、写嬢孃、写姐姐……这些人物在王安忆的笔下何止是骨骼清晰历历可数,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血肉的温度。作者对待他们,是针脚绵密的刺绣,是纤毫毕现的工笔细描,但写到这位母亲,就更像是逸笔草草点染写意,多靠周边人物的反应烘云托月。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吧,上部是作者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的“舒适区”,而下部是作者刚刚踏上的新疆土——一个笔耕不辍的作家,还愿意改变,愿意冒险,这很厉害。
读王安忆的小说,看凡夫俗子们的细碎缜密又不时露出破绽,会心处暗自发噱,有点像人类之眼看向蝼蚁,看它们秩序井然忙忙碌碌各有使命的样子,不免有几分可笑。可是,这又不是上帝之眼望向人间,因为我们始终知道自己也是这蝼蚁军团中的一员,只不过此时此地有片刻超然。而王安忆善于细密但永不会耽溺于细密,她的人物她的故事永远被置于天高地阔的大背景中,特写式的细密精明缜密总有一刻会现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仓惶无助,屈从,坚强。那时节,何止会心生怜悯,也将触动愁肠——有一种被看穿的畅快,以及被安慰的温暖:人生实苦,人间值得。
人在螺蛳壳里,也在历史的洪流中。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渺小又庄严。